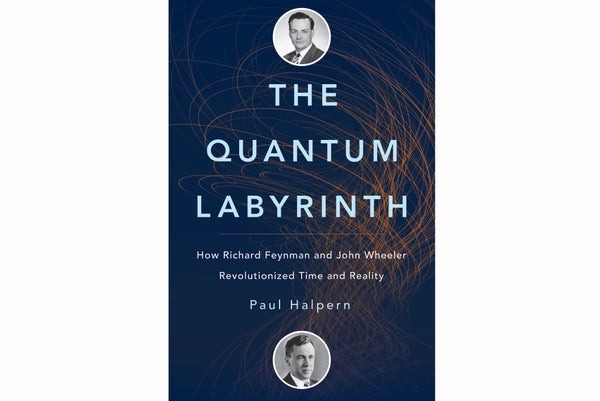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大众科学》的前博客网络,反映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大众科学》的观点
1927年,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布鲁塞尔的索尔维会议上开始与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就量子力学的意义展开著名的论战时,约翰·惠勒还只是个青少年。量子力学是对原子行为的物理描述。与经典的牛顿物理学不同,它涉及瞬时跃迁,由概率规则而非精确的、机械的定律决定。爱因斯坦反对量子理论的跳跃性、偶然性因素和其他不确定的方面,而玻尔则认为这些是可以接受的。当惠勒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至后期成长为一名物理学家时,他与两位辩论者都成为了亲密的朋友,欣赏他们有理有据的论点,并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来调和他们冲突的观点。
惠勒与爱因斯坦和玻尔一样,都对理论物理学的哲学基础有着深刻的理解。爱因斯坦对巴鲁赫·斯宾诺莎和恩斯特·马赫的阅读,使他倾向于客观、确定、原则上可由所有组件的本地观察者在任何时候直接测量的理论。相比之下,玻尔是东方哲学的粉丝,包括具有阴阳对立统一的道教,他在他的互补理论中接受了矛盾。根据这个概念,一个量子实体的行为,无论是像波还是像粒子,都取决于它的测量方式。虽然许多美国物理学家回避哲学,但身为两位图书管理员的儿子的惠勒却欣然接受。因此,虽然他倾向于玻尔的解释,但他发现两位思想家的观点都有其优点。
在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通过他向玻尔和其他人提出的思想实验论证说,即使量子力学与实验数据相符,它在根本上也是不完整的。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之所以不足,是因为它包括了实验者对方法和仪器的选择会影响某些参数是否具有确定值或是否模糊的情况。此外(正如 1935 年引入的纠缠概念所强调的那样),它是非局域的,这意味着量子态可能包括两个具有连接属性的事物,即使它们在物理上是分离的,甚至可能相隔很远的距离。每当玻尔驳倒他的一项思想实验时,爱因斯坦就会提出另一项。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未能提供自然的完整蓝图,这表明需要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论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开始寻找一种机械的、统一的场论来取代量子力学。这是一项将持续他余生的追求。
关于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关于当今塑造我们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惠勒于 1934 年在哥本哈根的理论物理研究所进行研究期间首次见到玻尔。1939 年 1 月,在惠勒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后,玻尔来到那里进行为期数月的研究。玻尔和惠勒共同开发了核裂变活化能模型,该模型预测了铀和钚的哪些同位素最容易裂变。那时,惠勒的重点更多的是实际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
当时,爱因斯坦是惠勒的邻居,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家里。这位流亡的德国物理学家在高级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最初位于普林斯顿的法恩大厅,直到建成专门的设施。惠勒的办公室也位于法恩大厅,与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以及玻尔在普林斯顿临时工作时的办公室)在同一楼层。爱因斯坦在默瑟街的房子离惠勒在战斗路的房子只有几个街区远。惠勒会说德语,并且性格愉快、随和,散发着友好的尊重——这些都是让爱因斯坦喜欢他的恰到好处的因素。
随着惠勒对玻尔和爱因斯坦都非常了解,并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导师,他开始思考如何调和他们截然不同的观点。虽然惠勒接受了玻尔的互补性,但他同意爱因斯坦的观点,即人类观察者(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做出触发量子“掷骰子”的决定)的作用是模糊的,甚至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人类难道不是也在深层受量子规则支配吗?
当惠勒的学生理查德·费曼开发出一种替代量子力学标准方法的激进方法时,出现了可能的调和机会。在费曼所谓的路径积分形式主义中,惠勒称之为“历史求和”,量子计算是通过对相互作用可能发生的各种替代路径的概率幅度进行加权求和来执行的。这就像计算一个人在通勤上班期间的总耗力,通过计算乘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车和并排步行等替代方案,就像所有这些都同时完成一样,而不是单独考虑它们。经典路径只是最有可能的路径。
惠勒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看待量子力学的更优越的方法,于是他顺便拜访了爱因斯坦的家,并与他深入讨论了费曼的方法。然而,这位固执的老物理学家并没有被说服。“我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爱因斯坦说。“但也许我应该犯我的错误。”
1955 年爱因斯坦去世后,惠勒继续努力在关于量子力学的各种观点中找到共同点。当他的另一位学生休·埃弗里特三世用他的通用波函数概念(后来被布莱斯·德威特称为“多世界解释”)消除了观察者的直接作用时,他很感兴趣。量子物理学将完全是确定性的,而不是“掷骰子”。唯一的难题是,每次量子测量时,宇宙都会分裂成无数种可能性。与“历史求和”将可能性融合为单一现实不同,这些将是它们各自独立存在的不同现实。观察者的有意识存在也会分叉,允许不同的副本体验不同的结果。因此,人类和粒子的命运将联系在一起,从而避免了对独立观察者的需要。
就埃弗里特的假设而言,是玻尔不肯让步。无论惠勒多么努力地说服玻尔,认为这是一个更全面的理论,玻尔都认为没有必要偏离互补性。惠勒试图用最不激进的方式来描绘埃弗里特的理论,但玻尔对此毫无兴趣。
惠勒最后一次尝试弥合裂痕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玻尔去世十多年后。惠勒通过“参与性宇宙”寻求自洽,在这种宇宙中,现在的人类观察可能会影响过去的量子结果。因此,互补性变成了一个闭环,其中过去观察到的事物塑造了整个历史,并最终塑造了观察者自身。惠勒称之为“自激电路”。他意识到,唯一缺少的是观察者存在的原因。“存在是如何产生的?”成了惠勒的终极问题。当他于 2008 年去世,享年 96 岁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