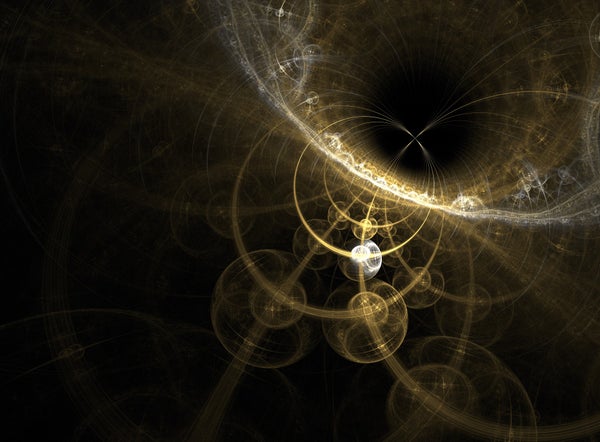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大众科学》的前博客网络,仅反映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众科学》的观点
1955年秋季的一个深夜,在几轮雪利酒后,丹麦物理学家奥格·彼得森在普林斯顿大学与两位研究生查尔斯·米斯纳和休·艾弗雷特辩论了量子物理核心的奥秘。彼得森当时在捍卫他的导师尼尔斯·玻尔的观点,玻尔是“哥本哈根诠释”的创始人,这是理解量子物理的标准方式。哥本哈根诠释以玻尔著名研究所的所在地命名,指出超微观的量子世界与我们日常经验的普通世界完全分离。
彼得森说,量子物理学仅适用于超微观领域,在那个领域,单个亚原子粒子会表现出其奇怪的把戏。它永远不能用来描述由数万亿个此类粒子组成的人、椅子和其他物体的世界——那个世界只能用艾萨克·牛顿的经典物理学来描述。而且,彼得森声称,这本身是由量子物理学决定的:一旦涉及的粒子数量变得巨大,量子物理学的数学就会简化为牛顿物理学的数学。
但艾弗雷特以酒精助兴的虚张声势,尖锐地抨击了彼得森所倡导的正统立场。艾弗雷特指出,量子物理学实际上并没有简化为大量粒子的经典物理学。根据量子物理学,即使是像椅子这样正常大小的物体也可能同时位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种类似于薛定谔猫的状况,被称为“量子叠加”。艾弗雷特继续说道,求助于经典物理学来挽救局面是不对的,因为量子物理学应该是一种更基本的理论,一种支撑经典物理学的理论。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未来能够继续讲述关于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
后来,在冷静下来后,艾弗雷特重新考虑了自己的立场——并决定加倍坚持。他扩展了那天晚上的论点,并将他对量子正统观念的攻击变成了博士论文。“现在是时候……将[量子物理学]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理论,而不依赖于经典物理学,”他在给彼得森的信中写道。
为了解决叠加问题,艾弗雷特提出了一个真正激进的想法,似乎更适合他在业余时间阅读的廉价科幻小说:他说量子物理学实际上暗示了无限多个几乎相同的平行宇宙,每当进行量子实验时,这些宇宙就会不断地相互分裂。艾弗雷特在量子物理学的数学中发现的这个奇异的想法后来被称为“多世界”诠释。
多世界诠释几乎立即遇到了阻碍,这个人就是艾弗雷特在普林斯顿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惠勒是一位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他在该领域之外并不广为人知,但他认识该领域内所有重要人物。他是玻尔的门生,也曾与爱因斯坦关系密切。在艾弗雷特出现在他家门前十五年前,惠勒曾指导年轻的理查德·费曼的博士学位;后来,他继续指导了数十位更著名的物理学家的博士学位(包括去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基普·索恩)。
艾弗雷特的奇怪想法最初对惠勒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有望将量子理论应用于整个宇宙本身,这正是惠勒迫切希望做的事情。但惠勒是一个政治动物,他担心因偏离哥本哈根所宣扬的量子正统观念而招致导师玻尔的愤怒。惠勒试图调和这一矛盾的做法非常直接:他前往哥本哈根,试图获得玻尔对艾弗雷特工作的祝福,将其作为官方哥本哈根量子理论性质路线的延伸。
事情进展不顺利。惠勒从哥本哈根写信给艾弗雷特,说要解决玻尔对艾弗雷特想法的批评“将需要大量的
时间,与像玻尔这样务实而强硬的人进行大量的辩论,以及大量的写作和重写。” 惠勒恳求艾弗雷特亲自来哥本哈根,并“与最伟大的战士[即玻尔]战斗”。
艾弗雷特对战斗或重写任何东西都不特别感兴趣。他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信心,并且没有被学术生涯的智力魅力所吸引。他更感兴趣的是金钱以及金钱可以带来的东西:美食美酒、物质享受和女人。他想要的是《广告狂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教授的办公室。在惠勒的信到达时,艾弗雷特已经找到了一份承诺给他这一切的工作:他已经在五角大楼找到了一份研究员的工作,在冷战高峰期推演假设的核导弹交换的后果。
当惠勒从欧洲回来时,他强迫艾弗雷特大幅修改了他的论文,并删除了几乎所有关于“世界分裂”的提及。一旦完成,艾弗雷特离开了普林斯顿,再也没有回到学术界。在后来的五角大楼工作生涯中,艾弗雷特考虑了核战争更可怕的可能世界,并继续与他人合著了关于放射性尘埃的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报告之一。
但艾弗雷特最终还是去了哥本哈根。1959年3月,当他在欧洲出差时,他去了丹麦,并向玻尔介绍了他的想法。正如艾弗雷特后来描述的那样,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艾弗雷特和玻尔都没有被说服。“玻尔的量子力学观点基本上被全世界每天从事量子力学研究的数千名物理学家完全接受,”当时也在哥本哈根的米斯纳说。“期望一个孩子通过一个小时的谈话就能完全改变他的观点是不现实的。”
艾弗雷特的作品陷入了深深的默默无闻之中。直到 1970 年代才被重新提起,即使在那时,也很难流行起来。艾弗雷特确实最后一次涉足关于他工作的学术辩论;惠勒和他的同事布莱斯·德威特邀请艾弗雷特在 1977 年德克萨斯大学就他的工作发表演讲。当时在奥斯汀的年轻物理学家之一是大卫·德意志,他后来成为多世界诠释的坚定倡导者。德意志回忆说,艾弗雷特“充满了神经质的能量,精神高度紧张,非常聪明”。“他对多重宇宙非常热情,并且在捍卫多重宇宙方面非常有力且微妙。”
德威特、德意志和其他人的工作使多世界诠释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变得越来越流行。但艾弗雷特没有活到看到多世界诠释达到目前的地位,成为哥本哈根诠释最突出的竞争对手。他于 1982 年因严重心脏病去世,享年 51 岁。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家人将他火化,并将他的骨灰放在外面与垃圾一起收集。但艾弗雷特好辩而顽皮的精神在他的理论中得以延续,这个理论诞生于 60 多年前的一场醉酒辩论,至今仍在物理学家中引发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