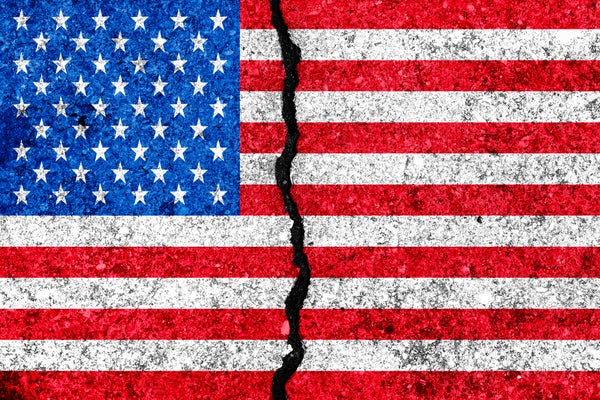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大众科学》的前博客网络,反映了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众科学》的观点
“首先是‘我的一代’,然后是‘我的世代’。现在我们有经验证据表明,我们生活在将被称为‘混蛋时代’或‘推特时代’的时代……”——性格心理学家布伦特·罗伯茨在推特上说
“我们的运动旨在用一个由你们,美国人民,控制的新政府取代失败和腐败的政治建制派。... 试图阻止我们的政治建制派,正是对我们灾难性的贸易协议、大规模非法移民以及使我们国家枯竭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负责的同一批人。... 唯一能阻止这个腐败机器的是你们。”——唐纳德·特朗普为美国辩护
当今世界存在许多分歧。但有一种分歧,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核心,有助于解释许多其他分歧。我指的是人格变异的根源,它内置于我们的 DNA 中:对抗性。通过真正关注这一特质,并了解对抗性如何与环境条件和信息传递相互作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今世界最突出的分歧之一:民粹主义。
首先,让我们深入了解对抗性的最新科学。
关于支持科学新闻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将帮助确保有关塑造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对抗性的科学
人格的对抗性-宜人性维度是人格五大维度之一。与人格的其他主要维度一样,这种特质在人群中呈正态分布。两个人在这个基本维度上的差异越大,另一个人的行为就越难以理解,尤其是在遵守社会规范和利他行为方面。
宜人性(对抗性的对立面)由两个主要方面组成:礼貌和同情心。礼貌反映了遵守社会规范、避免挑衅和剥削他人的倾向,而同情心反映了在情感上关心他人的倾向。在礼貌方面得分高的人专注于公平,而在同情心方面得分高的人更专注于帮助他人,尤其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在另一个极端,低礼貌水平的人(对抗性强的人)在攻击性测量中往往得分很高,而低同情心水平的人在同理心测量中往往得分很差。虽然礼貌和同情心可能会分开——例如,一个人在同情心方面得分很高,但在礼貌方面得分很低——但在普通人群中,礼貌和同情心密切相关,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宜人性的整体人格领域。
与所有其他人格变异一样,宜人性-对抗性维度的差异也反映在大脑中。从神经学角度来看,宜人性得分高的人往往表现出默认模式脑网络的更高激活,这与模拟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以及理解和分享他人情感体验所必需的不同类型信息的高级整合有关。宜人性也与情绪调节能力有关,特别是抑制攻击性冲动和其他具有社会破坏性的情绪。从神经化学的角度来看,宜人性涉及神经递质睾酮(与远离礼貌和趋向对抗性的倾向有关)和催产素(与同情心和群体内社会联系的倾向有关)。
对抗性-宜人性维度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很大的预测价值(不仅仅是在科学实验室中)。对抗性强的人更可能做出攻击性反应并在受到他人不公平对待时进行报复(尽管他们往往不太关心他人是否受到不公平对待)。在工作中,对抗性强的人在收到经理的愤怒讲话后表现优于高度宜人的人(这会激发他们),而高度宜人的人在经理表达对他们表现的满意后往往会提高他们的表现。
这种人格维度对政治也具有深刻的意义。更具对抗性的政治家获得更多媒体关注,并且比更宜人的政治家更常当选。在普通人群中,对抗性强的人更可能不信任政治,相信阴谋论,并支持分裂主义运动。
对抗性并非绝对的好或坏。丹尼尔·内特尔推测所有人格特质的进化都具有权衡取舍,这就是人格变异存在的原因。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宜人性既有好处(关注他人的心理状态;和谐的人际关系,有价值的联盟伙伴关系),也有代价(容易受到社会欺骗和剥削;未能最大化自私的优势)。然而,由于这种特质存在如此广泛的变异,高度对抗性的领导人可以通过他们的言辞和信息传递来唤起和影响大量在这种特质上得分很高的人。
对抗性与民粹主义的共鸣
心理学界越来越认识到,人格特质与领导人的信息传递相互作用。吉安·卡普拉拉和菲利普·津巴多指出,“政治家的关键技能是……通过识别和传达在特定时间对特定选区最具吸引力的个人特征,来说‘人格语言’”。他们发现选民会选择与其自身人格相匹配的政治家。
帕蒂·瓦尔肯堡和乔亨·彼得也提出了他们的媒体效应差异易感性模型(DSMM),该模型认为,信息的措辞和框架对具有特定性格的人比对其他人具有更大的认知和情感影响。例如,希望的信息可能对那些更容易体验积极情感和热情的人更具吸引力,而变革的信息可能在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中更具吸引力。
然而,也许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互动是对抗性与民粹主义之间的互动。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反建制信息和对人民中心重要性的关注。反建制信息将政治精英描绘成腐败和邪恶,并且对“纯洁人民”的利益漠不关心。约翰·朱迪斯和鲁伊·特谢拉认为,民粹主义者的本质分歧是“人民与当权者”。
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政治传播学教授伯特·巴克及其同事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规模最大、最系统的调查:当对抗性公民收到反建制信息时会发生什么?他们发现,民粹主义者的反建制信息最能引起高度对抗性人群的共鸣,这一观点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发现在三大洲的七个国家得到证实。对抗性预示着对右翼(特朗普、英国独立党、丹麦人民党、自由党、瑞士人民党)和左翼(波德莫斯、查韦斯)民粹主义者的支持。
他们还使用生理测量方法,确定了这种联系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情感过程。研究人员使用皮肤电导测量(捕捉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发现人们对与其人格相符的政治信息反应的唤醒程度有所提高。特别是,对抗性强的人发现反建制信息令人兴奋,而高度宜人的人则发现亲建制信息令人兴奋。
这很重要,因为情绪在决定政治沟通如何影响我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些更容易被特定信息唤醒的人更有可能记住它,并在长期内再次寻求该信息。这些发现表明,政治家可以通过提供与选民人格产生情感共鸣的信息来对选民施加重大影响。
他们还研究了威权主义。威权主义概括了对社会秩序、结构和服从的偏好。先前的研究表明,高度威权主义者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较少的容忍度,并支持具有右翼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政党。与此一致,巴克及其同事发现,虽然威权主义并不能预测反建制信息,但它确实能预测对特朗普和英国独立党的支持,以及对任何持有强烈反移民立场的候选人的支持。这些发现表明,民粹主义还有第二条途径,即通过与右翼民粹主义相关的特定意识形态。
对抗性-宜人性分歧的意义
这些天似乎有些不同寻常。根据您的观点(和个性),事情要么更“险恶”,要么更“革命性”。但我认为我们都可以同意,仅仅在过去几年里,政治格局和话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直存在党派分歧,但似乎有一种不同类型的分歧更加突出,即人民与政治家之间的分歧。正如荷兰政治学家卡斯·穆德指出,“如今,民粹主义话语已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的主流。”
重要的是要强调,民粹主义是一种超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研究表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是宜人的,但他们宜人的方式不同:宜人性的礼貌方面与保守的观点和更传统的道德价值观相关,而宜人性的同情心方面与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相关。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以互补;社会既需要那些深切关心每个人的公平和社会稳定掌权者,也需要那些更专注于帮助有需要的人。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仅凭民粹主义本身并不一定危险。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将包括那些挑战政府并批评当权者的人。特别有问题的是,当一位高度对抗性的领导人使用言辞来唤起其他对抗性人群的情绪,并团结他们支持特定的有害意识形态时。这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即掌权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缺乏同理心、视角转换能力以及控制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动所需的自我控制能力。
当然,并非所有支持民粹主义的人都是对抗性强的人。人们支持民粹主义者有很多原因。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试图理解许多特朗普选民在投票时的想法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原因包括“停滞不前的工资、失去家园、难以捉摸的美国梦以及在他们的生活背景下有意义的政治选择和观点,撕裂了他们的生活。”
然而,在社交媒体、YouTube 和另类媒体上,对抗性强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认为自己比政府“精英”有更好的答案,并受到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信息的鼓舞和唤醒,从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力。人们变得更容易接受民粹主义的关键原因,与其说是社会经济因素是民粹主义吸引力的最突出解释(巴克及其同事实际上在其研究中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不如说是人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并且更自由地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民粹主义的吸引力部分归因于 1960 年代日益增强的平均主义,其结果是今天的公民对政治家期望更高,并且感觉自己更有能力评判他们的行为。
总的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正如卡斯·穆德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公民认为自己对政治家的所作所为有很好的了解,并且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与此同时,实际上更少的人想要通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做得更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在撰写时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近半个世纪的调查提供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公民并不重视实际参与政治生活。”
有趣的是,民粹主义支持者实际上并不想由“普通人”领导;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望由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来实施。穆德发现,大多数民粹主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局外人精英”;他们与精英阶层联系紧密,但他们不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只是不想受“异己”精英的统治,他们的政策不能直接满足他们自己的愿望和关切。
这项研究非常重要,需要牢记在心,因为它看起来,为了推行更激进的政策而使用民粹主义言论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正如穆德观察到的,由于多种因素,“民粹主义将成为未来民主政治中更常见的特征,只要‘沉默的大多数’的重要部分感到‘精英’不再代表他们,它就会爆发。”
理解人格差异可能不是理解民粹主义吸引力的唯一因素,但为了国家和世界的缘故,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