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大众科学》的前博客网络,仅反映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众科学》的观点
当我们进行创造时,我们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当我们从事艺术与科学时,我们的大脑看起来有何不同?天才创造者的大脑与我们其余人有何不同?研究创造性大脑有哪些局限性?创造力的神经科学正在蓬勃发展。现在有一个学会(以及一个年度会议)、一本编辑卷、一本手册,以及现在一本关于该主题的完整教科书。安娜·亚伯拉罕汇集了众多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撰写了一本精彩的资源,涵盖了该领域一些最热门的话题。她很荣幸地接受了我的问答。请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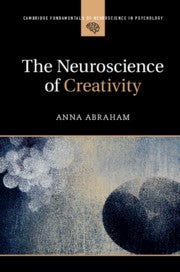
SBK:您是如何对创造力的神经科学产生兴趣的?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当今塑造我们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AA:我一直对创造力感到好奇。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想我只是想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这种奇妙能力的奥秘。特别是,我希望找出是什么让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具创造力。当我在 2000 年代初期看到有机会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研究任何我选择的主题时,我全力以赴——这是一种令人兴奋且有前景的方法,直到那时才被有限地用于探索创造性思维。
SBK:什么是创造力?该领域是否对创造力有一个统一、公认的定义,您对此感到满意吗?
AA:当谈到样板定义时,该领域出人意料地达成了一致。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创造力有两个核心要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反映了我们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原创的、不寻常的或新颖的想法的能力。第二个要素是,这些想法还需要令人满意、适当或适合所讨论的背景。我对这个定义相当满意,但对其如何指导科学探究并不满意。仅凭与创造力相关的许多经验发现与原创性(创造力的核心特征)无关,而是与诸如流畅性和灵活性等相关因素有关这一事实,就表明了我们科学论述中普遍存在的脱节。
SBK:全面定义创造力有哪些挑战?
AA:核心挑战之一是拥有一个可以令人满意地应用于创造力的所有表现形式的定义,无论被判断的“对象”是艺术作品、科学理论还是公共政策策略(等等)。另一个挑战源于在判断和将“对象”归类为创造性较少或较多时固有的主观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使用的是什么衡量标准?它与您使用的衡量标准有多相似?我是否有足够的背景知识或必要的专业知识作为评判者来做出该决定?即使我做到了,我对知识的限制或我的思维方式如何限制我识别他人创造力的能力?
SBK:创造力可以衡量吗?
AA:创造力的某些方面可以衡量——是的。问题是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工具来实现这个目的。
SBK:哪种创造力方法最适合神经科学的视角?
AA:有影响力的“4P”概念化指的是研究创造力时可以采用的方法。关注促进或阻碍创造力的因素的方法可能是外部的,因为它们是环境(压力/地点)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内部的,以体现个人的特征和技能(人)。这些方法与从创造性构思过程中发生的心理操作(过程)及其输出(产品)的角度研究创造力截然不同。神经科学的视角属于更广泛的生理学方法的范畴,我坚持认为这构成了创造力的第五个“P”,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方法,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见解,可以提供关于创造力的信息。我写的这本书就是这种观点的证明。
SBK:神经科学家研究创造力时面临哪些独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人类心理功能的其他复杂方面不会遇到,而后者更容易进行客观的科学探究?
AA:有很多。最重要的问题是无法提示创造力。对于许多相当复杂的功能,您只需用适当的问题提示响应即可。可以确定一个人是否记得某个特定事件(您上次生日做了什么?)、知道一个事实(土星有多少个环?)、经历过刺激(您能听到警笛声吗?)、享受某种体验(您有多喜欢骑自行车?),等等。但是,正如我们许多人通过自己的经验所知,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刺激自动引发一连串的创造性思维。当我们被要求这样做时,我们可能在努力变得有创造力,但这与具有创造力不同。
SBK:“大脑到过程”和“过程到大脑”的创造力解释之间有什么区别?
AA:那里的区别在于在揭示创造力的大脑基础时探索的方向。如果您的起点是与创造力特别相关的过程,例如即兴创作,并且您检查了它的脑部相关性,那么您将进行过程到大脑的探索。也可以反过来——从大脑结构或大脑活动模式的层面开始,这些结构或模式与创造力特别相关(或可能相关)。假设我们回到过去,并设法获得了莫扎特的尸检大脑。在检查后,我们发现莫扎特大脑的缰核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典型的。我们可能会认为这足以让我们假设莫扎特在作曲方面的惊人能力可能源于他大脑中这种神经解剖学结构的非典型性。这将是“大脑到过程”探索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在检查爱因斯坦的大脑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SBK:为什么“创造性右脑”的神话仍然存在?这个神话有任何真实性吗?
AA:像大多数持久的神话一样,即使最初的想法发展与某种真实性有关,如此声明的主张也相当于一种懒惰的概括,而且是不正确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脑的右半球不是一个独立的器官,其运作可以与左半球的运作隔离开来考虑。断言左脑没有创造力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即使是最早探索大脑偏侧化与创造力关系的学者也强调了两个半球的重要性。事实上,与其他高度偏侧化的心理功能相比,这被认为是创造力的独特之处。在一个见证了一个半球对许多功能的主导作用的时代,左半球因其在语言等复杂功能中的关键作用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强调也需要认识到右半球对创造力等复杂功能的重要性,这种逆流而上的努力在一段时间内被错误地翻译成唯一的“创造性右脑”迷因。这通常是在制作易于理解的口头禅来传达科学发现时发生的事情。
SBK:额叶功能与创造力相关的复杂性有哪些?
AA:试图确定额叶功能与创造力相关的性质,常常感觉像是在抓住一条滑溜的鱼。首先要记住的是,它是一个巨大的异质结构,约占新皮层的三分之一,并且当我们进行创造性构思时,额叶的不同部分会参与其中。额叶功能的另一个特点是,对该大脑区域不同部位的损伤会导致创造性表现方面的一些劣势,但也会带来特定的优势。例如,对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损伤与洞察力问题解决方面更大的成功有关,而对前额极区域的损伤与在创造新事物时更强的克服显着示例的约束的能力有关。创造力方面的优势和劣势是否源于正在检查的创造性认知的具体方面,或源于大脑中病灶部位的位置和程度,或源于相关更广泛的大脑网络的动态,目前尚不清楚。
SBK:洞察力、类比和隐喻认知处理的不同大脑相关性是什么?
AA:所有这些创造性认知操作都具有重叠的大脑相关性,但不同之处在于在每个过程中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定大脑区域。前额极的作用在类比推理中得到强调,外侧下额叶回在隐喻处理中得到强调,颞上回前部在洞察力中得到强调。明确肯定这些大脑区域对这些过程各自的特殊相关性,将是在一个实验范式中检查所有这些过程。
SBK:当我们以创造性模式与非创造性模式运作时,我们的大脑中会发生什么?
AA:到目前为止,我们才刚刚触及这个大问题的表面。显而易见的是,触发创造性模式而非非创造性模式的大部分因素是情境性的。创造性模式适用于不清晰、模糊和开放式的环境。非创造性模式则相反。因此,非创造性模式涉及坚定地沿着“最小阻力路径”穿过预期、显而易见、准确或高效的黑白区域。而创造性模式则涉及避开最小阻力路径,冒险进入荆棘丛中,可以这么说,努力在意外、模糊、误导性或未知的灰色区域开辟一条新路径。我们对非创造性模式下大脑中存在的接受-预测循环了解很多。我们对创造性模式下存在的探索-生成循环知之甚少。但我们所知道的非常有趣。例如,在非创造性模式下以受限方式运行的几个大规模大脑网络,在创造性模式下以整合和动态的方式参与其中。将创造性思维视为一个多方面的结构,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特定大脑区域在创造力的特定方面(如洞察力、意象、类比推理、克服知识约束、概念扩展等)的作用的理解。最发人深省的发现之一是,尽管神经水平存在紊乱和退化,我们仍有能力从事创造性活动。这证明了大脑在实现自我表达和沟通方面的抗紊乱能力。
SBK:例如,您如何确定一个领域(如音乐和音乐性)的哪些方面是创造性的,哪些方面是普通的?
AA: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根据所采用的分析或反思水平,有几种潜在的答案。在您提到的音乐和音乐性领域,可以区分聆听、表演、即兴创作和作曲的形式。如果采用创造力的标准定义,那么即兴创作和作曲将被认为是最明显的创造性形式,因为两者都证明了原创性反应的潜在发明。当然,这里必须记住一些注意事项:例如,并非所有的即兴创作都必然是创造性的。但也有充分的理由将音乐表演也视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因为原创性反应不仅可能在发明层面,也可能在表达层面。毕竟,这是为什么一些音乐家可以比其他音乐家获得更高票价的关键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在诠释和表达方面的原创性。一些学者甚至更进一步,声称即使是听音乐的行为也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这是因为辨别他人反应模式(通过音乐发明/表达)中的原创性的能力,必然涉及在此过程中扩展自己的概念边界。
SBK:大脑可塑性真的可能吗?如果可能,程度如何?创造性思维如何既能诱导又能由大脑可塑性引起?
AA:大脑可塑性是一个事实。我们的大脑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在变化,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从我们永不停止学习的日常观察中得到证明。大脑可塑性的程度更难定义,并且尚未经过系统地研究。创造性思维涉及发现新颖的联系,因此与学习密切相关。亚瑟·柯斯特勒在几十年前就非常漂亮地指出了这一点:“创造性活动是一种学习过程,其中教师和学生位于同一个人身上。”
SBK:多巴胺、神经功能和创造力之间有何关系?
AA:有间接证据表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很有希望,但有必要进行进一步和更直接的调查以确定这种关系的性质。艾丽斯·弗拉厄蒂在 2000 年代初期最突出地指出了多巴胺对创造性驱动力的动机方面产生影响的观点。卡斯滕·德·德鲁领导的研究小组的当代公式强调需要区分前额叶多巴胺和纹状体多巴胺,因为它们分别促进创造性构思的不同方面,即持久性和灵活性。
SBK:一般来说,艺术参与(创作旋律、写诗、绘画或编排舞蹈序列)的神经学相关性与我们产生新理论或科学假设时大脑中发生的情况有何不同?
AA:我们对科学创造力的神经学相关性知之甚少。它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直接调查。但我们可以从我们对不同类型的推理和问题解决过程的大脑基础以及行为研究的了解中得出合理的期望。后者指出,积累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关注意外事件以及工作环境中群体因素的相关影响非常重要。关于不同艺术形式的创造力(音乐、文学、动觉、视觉)的研究也类似,它们强调相关的感知、意象、认知和运动技能如何随着专业知识的提高而得到增强,独特的流动体验以及外感受因素和内感受因素在创造性表演期间的重要活力。因此,这些功能背后的相关大脑网络也与此有关。还必须记住,艺术创造力形式在创造性体验的时间特性、与创造性实践相关的社会隔离程度、创造者-接受者关系、精神疾病倾向等方面存在若干差异。
就目前而言,关于不同创造性领域的创造力的大脑基础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主要是因为神经科学地检查特定领域的创造力形式存在严重挑战。它们通常涉及粗大运动(动觉创造力)或精细运动(音乐创造力、文学创造力、视觉艺术创造力),而大多数神经科学方法不利于大量运动。时间因素也在这方面构成了重大障碍。神经科学方法非常擅长捕捉从短期现在的神经活动中得出的大脑工作原理。但是,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一次精湛的表演或一个新颖的科学理论的创作都需要在较长且可变的时间内完成。因此,这些的神经基础鲜为人知。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能够使用间接方法挖掘跨领域的创造性过程方面富有创造力。因此,一幅引人入胜的图景正在慢慢展开。
* SBK:以下仅列出部分目前正在尝试解开创造性大脑奥秘的杰出科学家:罗杰·比蒂、马蒂亚斯·贝内德克、雪莱·卡森、伊万杰利亚·克里西库、安德烈亚斯·芬克、莉安·加博拉、亚当·格林、伊曼纽尔·尧克、雷克斯·荣格、詹姆斯·考夫曼、约德·肯内特、西蒙·基亚加、查尔斯·林姆、阿基·尼古拉迪斯、丹尼尔·沙克特、光武内、奥辛·瓦尔塔尼安、因德雷·维斯孔塔斯、达里亚·扎贝利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