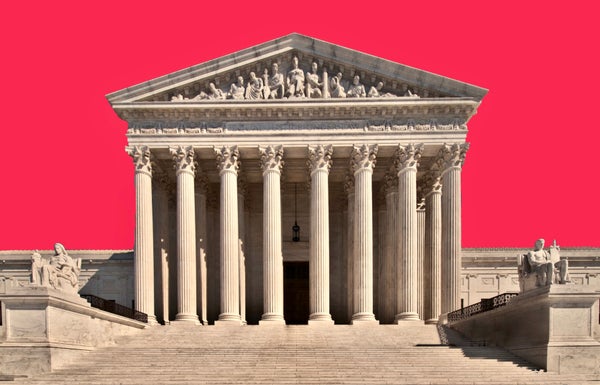堕胎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我理解。我记得当我还是妇产科住院医师时,我告诉我的主管医生,我会学习进行堕胎的技能,但可能毕业后不会提供堕胎服务,因为这样做让我“有点不舒服”。
我的主管医生回应我:“你认为女性有权接受这项手术吗?” 我心想,“嗯……是的,当然。”
随着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的泄露的裁决,最高法院已表明其愿意在最高法院大楼里优雅伫立的司法女神雕像的天平上放置一块沉重的砖头。法律的目标,如同医学一样,应该始终是在利益和危害之间找到平衡。大法官们完全站在了危害的一边。
关于支持科学新闻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平衡天平将需要协调一致和持续的努力。大多数美国人处于堕胎辩论的“泥泞中间”,可能不愿涉足充满争议的水域。再说一次,这种犹豫是可以理解的。堕胎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被动的人不能再这样了。如果这是你,现在还不算晚。让你的立法者知道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你的家人和朋友进行艰难的对话,讨论你为什么支持身体自主权。向组织捐款,以支持他们正在做的这项工作。
原因如下: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医生,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提供堕胎服务时,我的主管和我讨论了我可能负有道德和伦理义务,尽我所能确保这项手术是可用的。因为这与我无关,与我的舒适无关,与你无关,与任何人无关,只与寻求护理的人有关。因此,将近 20 年后,除了产前护理和复杂妊娠分娩外,我现在还提供堕胎服务,并教新医生如何进行堕胎。
我这样做是因为人们有权接受这项手术,而且还因为这句医学格言引起了我的共鸣:“愿我在病人身上看到的,永远只是一个痛苦的同类。” 这并不是暗示每一个堕胎决定都必须是痛苦的(尽管有些是),而是提醒人们将病人的需求放在首位。
我有一个有点天真的想法,如果反堕胎运动者能在我的办公室里待上几天,他们就会开始理解了。虽然这种白日梦可能显得幼稚,但事实是,许多自认为是“支持生命权”的患者在得知意外怀孕的消息后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向我表达了他们对这些细微问题的新的理解。他们现在可以看到他们以前支持的法律的危害。
我之前写过关于如何提供既尊重生育又维护个人不怀孕权利的医疗护理,这并非矛盾。仁慈、不伤害、公正和自主这些公认的医学伦理原则迫使我提供全方位的生殖保健服务。如果关于多布斯案的泄露意见成立,它将阻止我提供全套产科护理,并颠覆 50 年来维护终止妊娠权利的先例。该案件对 2018 年密西西比州妊娠年龄法案提出质疑,该法案禁止妊娠 15 周后堕胎,几乎没有例外。请愿者还要求法院推翻确立妊娠前可行性堕胎宪法权利的先例,即罗诉韦德案和东南宾夕法尼亚州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的最终结果。各州现在将成为堕胎的主要立法者,并且可以强迫人们违背意愿生育。超过 20 个州已经制定了堕胎禁令,旨在如果法院裁定这些法律符合宪法,则迅速生效,其中最严格的禁令几乎完全禁止堕胎。
对于任何重视身体自主权、政教分离以及政府干预科学和医学的人来说,这都是可怕的消息。虽然我们不能从这场辩论中消除个人价值观和道德观,但如果我们接受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的前提,那么值得研究堕胎限制为何有害的科学依据。
多项研究证实,堕胎限制弊大于利,堕胎是安全的,而经常被引用的关于堕胎对心理健康有害的担忧是不真实的。这些研究中最著名的是为期十年的转向研究,其主要发现是,接受堕胎不会损害健康和福祉,但事实上,被拒绝堕胎会导致更糟糕的财务、健康和家庭结果。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将妊娠持续到足月分娩比早期合法堕胎危险 14 倍。虽然我们应该努力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尤其是在有色人种女性中,但事实是,怀孕(或被迫寻求不安全或非法堕胎)始终比安全进行的堕胎风险更高。
堕胎限制的危害是主流医学协会反对堕胎限制的原因。例如美国妇产科学院、母胎医学学会、美国儿科学会、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和美国家庭医师学会。美国医学会已表示反对最严格的法律。这些不是激进的边缘组织,而是由居住在您的社区并每天为您提供护理的医生组成的团体。
自 1973 年和 1992 年最初的堕胎裁决以来,技术一直在进步。医疗和外科堕胎的新技术不断降低已经很低的并发症发生率。家用妊娠试验变得越来越敏感,使人们无需就医即可识别怀孕。超声波和遗传学诊断技术呈指数级扩展,可以检测出 1973 年出生后才会知道的并发症。
当我们面临反堕胎州立法的冲击时,我们应该准备好一个想法,即如何最好地平衡天平,以提供最大的利益和最小的危害。作为一名致力于帮助孕妇和婴儿获得最佳结果的医生,我认为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是取消对堕胎的所有限制。这不是一个极端的立场。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得出结论,在怀孕的某个时间点之后限制堕胎并限制终止妊娠的理由是适当的,但怀孕是最复杂的生物学过程之一——因此,它可能出错的方式千差万别且复杂。一个人与医生一起做出的决定需要对个人价值观和情况进行细致的考虑,而不是可以立法的概括性方法;这是罗诉韦德案中论证的一部分。
即使是最高法院先前裁决所依据的“活力”概念,也因医学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模糊和动态。任何胎儿在子宫外作为新生儿存活的可能性都是基于许多因素的估计。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预后将会改变。“活力”是一个糟糕的法律标准。如果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在泄露的意见中做对了什么,那就是放弃将活力作为基准。
教条式的法律假定了一种在临床医学现实中很少存在的确定性。它们未能考虑到许多疾病预后的范围,以及社会心理环境的复杂性、精神健康和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不均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结果。立法者不可能对必须存在的每一种情况或例外情况进行立法,以防止有时会造成的重大伤害和/或痛苦。生物学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在取消堕胎限制后,我们接下来应该消除其他护理障碍。正如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限制选择的不仅仅是法律。如果你负担不起堕胎费用,无法请假,没有交通工具,或者有无数其他系统性限制,那么堕胎合法也无济于事。海德修正案禁止联邦政府资助的保险(如医疗补助)支付堕胎费用,需要彻底废除。FDA 对米非司酮(一种常见且安全的堕胎药)的不必要限制也必须取消。我们应该支持和促进许多优秀的组织,帮助人们获得护理并消除障碍。最后,由于生殖选择是关于选择,我们需要建立系统来支持选择继续怀孕和/或养育子女的个人。以上所有这些都不需要最高法院的裁决。许多可以而且应该由国会立法或由行政命令实施。
除了天平之外,司法女神还握着一把双刃剑。她蒙着眼睛。看来我们最高法院不会负责任地运用这把剑来处理堕胎问题,而一些大法官在身体自主权问题上蒙着的眼罩需要摘下来。维护堕胎权利的工作属于每个人——不仅仅是那些可以怀孕的人。我的病人应该在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身体做出决定。你也是如此。
这是一篇观点和分析文章,作者或作者表达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大众科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