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与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更古老。例如,公元前 68 年,罗马城市奥斯蒂亚是世界上最早的超级大国之一的重要港口,被一群暴徒纵火焚烧。他们摧毁了领事战争舰队,并且相当尴尬地绑架了两名高级参议员。恐慌随之而来——同样的恐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重演,这要归功于诸如爱尔兰共和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基地组织以及最近的 ISIS 等恐怖组织。在撰写本文时,世界在 20 天内目睹了三起重大恐怖袭击——贝鲁特、巴黎、圣贝纳迪诺——紧随其后的是伊斯坦布尔、喀布尔、迪夸、尼日利亚和其他地方发生的额外暴行,每次都是由伊斯兰极端分子实施的。正如 19 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西奥多·蒙森描述奥斯蒂亚的罪犯是“来自各国的破落户”组成“一个具有特殊集体精神的海盗国家”一样,今天的政治领导人通常将恐怖分子描述为精神错乱、精神失常或纯粹的邪恶。
那么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相当多。但是,他们冷静的观察似乎被参议员、名人和其他人对伊斯兰教发动他们自己的修辞圣战的过于熟悉的合唱声淹没了。当我们继续努力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挑战时,也许我们都应该进行一次大脑检查。也许我们应该倾听来自我们一些实验室的更安静、更敏锐的声音,而不是鹦鹉学舌地重复那些好辩的评论员和好战的吹牛大王刺耳的叫嚣。
或者更确切地说,也许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这样做。
关于支持科学新闻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将有助于确保有关塑造我们今天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诚然,科学和政治常常成为不舒服的床伴。历史证明,两者之间令人遗憾地发生了一系列即兴的幽会,孕育了不人道的意识形态。想想种族灭绝的雅利安至上主义者残酷地绑架了主流进化论,并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媒介将其令人作呕地重塑为纳粹主义教条。然而,面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日益高涨,如果我们科学家只是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似乎就太失职了。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挺身迎接将社会心理学置于反恐战争中心舞台的挑战。我们不会假装这很容易:多年来,该领域产生了大量经过经验洗涤的智慧。但在与一个国际专家小组进行热烈的讨论之后,我们集中研究了来自社会认知到冲突解决等广泛研究领域的七项典范研究。我们相信,每一项研究不仅对政策决策具有直接意义,而且对我们所有身处快速变化世界中的个人也具有直接意义。
1. 你和我在一起吗?

哈里·马尔特
研究: “虚假共识”效应:社会认知和归因过程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偏差。 李·罗斯、大卫·格林和帕梅拉·豪斯(1977 年)
研究领域: 社会认知
概述: “永远记住,你是绝对独特的,”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俏皮地说。“就像其他人一样。” 她说得很对。难道我们不都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吗?这项经典研究考察了我们有多容易受到一种错觉的影响,即我们的选择、判断、感受和信仰也反映了其他人的想法。
方法论: 调查人员向大学生展示了真实和假设的任务(例如,他们是否愿意在校园里戴着三明治板,作为态度改变研究的一部分?),并要求他们表明自己的反应。他们还要求他们估计他们认为会以相同方式回应的其他学生的百分比。
发现: 参与者始终认为他们自己的个人判断广泛代表了他们同学的观点。这种现在已得到充分证实的效应已被称为虚假共识偏差。
启示: 这个实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在“做自己”这件事上,我们人类既想拥有蛋糕,又想吃掉它。我们陶醉于成为我们自己的人的想法,但我们的大脑是为群体生活而生的。因此,自然选择想出了一个漂亮的小应用程序,它为我们提供了与其他人一样的错觉。它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选择是理性的和适当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渴望的社会认知自主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运行良好: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政治家在选举前经常表现出如此奇怪、毫无根据的乐观情绪?但偶尔,当一点点好战的信念转移成恶性意识形态肿瘤时,共识的错觉可能会变得致命。这在群体中尤其危险;在没有任何其他观点挑战的情况下,肿瘤会迅速变得具有攻击性。
政治家和公众必须愿意质疑他们的假设——关于恐怖主义、关于移民、关于宗教——以免他们陷入虚假共识的陷阱。
2. 看到什么,说什么

哈里·马尔特
研究:群体对旁观者在紧急情况下干预的抑制。 比布·拉塔内和约翰·M·达利(1968 年)
研究领域: 群体决策
概述: 为什么人们有时在面对危险时无所作为?这项来自社会心理学史册的殿堂级研究调查了其他人的存在对紧急情况下决策产生的强大而令人惊讶的影响。要采取行动,个人必须首先注意到事件,将其解释为紧急情况,并承担个人责任进行干预。该研究表明群体动力学如何打破该链条中的环节。
方法论: 被分配完成问卷调查的男大学生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开始充满烟雾的房间。他们是独自一人,三人一组,或者由两名参与实验且没有反应的人陪同。有人会离开房间报告烟雾吗?
发现: 大约 75% 的单独参与者报告了烟雾,而三人一组的参与者只有 38% 报告了烟雾。那些由冷漠的研究同伙陪同的受试者呢?只有 10% 的揉眼睛、挥舞烟雾的斯多葛派人士拉响了警报。
启示: 这项研究表明,对于任何可能取决于不熟悉的行为或决定的行为,我们都会参考其他人。不幸的是,紧急情况通常始于模棱两可、可能无害的情况。而且,由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避免尴尬的热情支持者,因此我们会参考他人的行为来告知我们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们不行动,我们就不行动。
因此,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关键挑战是促进心理学家所说的“人际赋权”的文化传播:我们都对影响他人福祉以及我们自己福祉的结果负责的意识。简单的干预措施包括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张贴海报,例如,海报上可能显示一个可疑的包,并警告说:“不要指望别人。这取决于你!”
我们都会从定期提醒中受益,这样我们的旅鼠式倾向就不会妨碍挫败恐怖袭击。同样,在极端主义团体内部,同样的抑制可能也在起作用,阻止成员质疑令人发指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为就变成了常态。
3. 群聚和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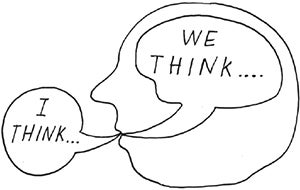
哈里·马尔特
研究:通过了解你是谁来了解该思考什么:自我分类与规范形成、从众和群体极化的性质。 多米尼克·艾布拉姆斯等人。(1990 年)
研究领域: 信仰形成
概述: 有时我们想要第二个意见,但事实证明,我们对信任谁来提供意见是有选择性的。这种偏见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甚至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现实的感知。本文中的实验表明,我们如何错误地认为与我们认同的人比我们归类为“不同”的人更清楚地了解现实。
方法论: 调查人员向一组六名参与者展示了经典的视错觉,即自动运动效应,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在这种错觉中,一个静止的光点似乎在不同的方向移动约 15 秒。在一系列试验中,参与者必须大声估计他们认为聚光灯从起点到达的最远距离。但有一个陷阱。该小组的一半是秘密特工,研究人员向他们介绍了将真实参与者的判断延长五厘米。此外,实验人员巧妙地操纵了其中一些秘密特工的社会身份,使他们或多或少地类似于真正的参与者。群体“归属感”会导致参与者增加他们的估计以匹配渗透者的估计吗?
发现: 绝对是!参与者和秘密特工之间的明显差异越大——他们看起来有多么不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估计差异就越大。
启示: 这里有两个主要信息。第一个是我们效仿我们认同的人的榜样,而无视其他人。因此,围绕社会差异的政策框架至关重要。温和、中年的伊玛目谴责狂热、年轻的原教旨主义者固然很好,但年轻人什么时候认同过当权派呢?第二——社区和宗教领袖请注意——当我们不确定如何处理给定的情况时,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社会群体中的人来决定什么是适当的反应。在健康的文化熔炉中,这很好。但是,当群体开始与传统社会隔离时,这种天生的“群聚和规范”倾向可能会形成小团体、邪教和其他类型极端分子的跳板。
以下两点:首先,我们的领导人必须积极寻求来自他们自己群体以外的专家的证据和建议。其次,他们应该尝试找到阻止群体漂向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孤立状态的方法。
4. 部落联系

哈里·马尔特
研究:社会分类和群体间行为。 亨利·塔吉费尔等人。(1971 年)
研究领域: 群体动力学
概述: 如前所述,我们人类天生就是群体的一部分。但是,自然选择设法多么一丝不苟地安装了我们的部落电路,以及它的开关多么容易被拨动,直到这篇经典论文巧妙地将克利置于康定斯基之间才完全显现出来。
方法论: 志愿者评估了不熟悉的、未署名的艺术品,然后在一个完全捏造的、任意的基础上被分成两组:一半人被告知他们喜欢的画作是艺术家保罗·克利的;另一半人听说他们更喜欢瓦西里·康定斯基的作品。事实上,分配是完全随机的。一旦被放入这些毫无意义、零热量的群体中,并且不知道还有谁在其中,每个参与者都被赋予了一项完全不相关的任务:向两位同伴研究对象分配积分——这些积分可以转化为金钱。这些同胞是匿名的,但以下身份标签除外:克利小组或康定斯基小组的成员。参与者是某个群体而非另一个群体的简单事实会影响他们对积分的分配吗?
发现: 参与者慷慨地向自己群体的成员发放积分——以及获得经济奖励的前景——并坚定地拒绝向另一群体的成员发放积分。公平荡然无存。那是“我们这群人对抗另一群人”。句号。
启示: 不难理解群体内偏见的威力。您所要做的就是出现在足球比赛中或登录 Facebook。但常识不太容易接受,而本文如此优雅地证明的是,这种忠诚可以在没有终生效忠于野马队、巨人队或老鹰队——或伊斯兰教、基督教或犹太教的情况下获得。将人们归类为所谓的最小群体——除了名称之外,没有任何区分特征的群体——足以唤醒一种立即的、可能是祖先的对积极的群体内独特性的渴望。我们与他们的心态——所有歧视和偏见的心理零点。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利用这种内置的成为“梦之队”一部分的动力来造福社会。我们需要减少我们-他们区分的心理契合度的策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弹药:关注每个人作为独特的个体;关注超级我们,一个将每个人捆绑成一个群体的类别(例如,人类);或者放大我们类别中与他们类别相交的各种类别(例如,性别、年龄和国籍,甚至是对篮球的热情)。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消除人们将他们所有的心理积蓄都押在那唯一一把存在主义扑克牌上的倾向。
5. 极端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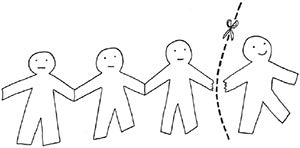
哈里·马尔特
研究:为自己的群体而死和杀戮:身份融合缓和了对群体间版本的有轨电车难题的反应。 威廉·B·斯旺等人。(2010 年)
研究领域: 社会身份
概述: 许多人对“重要”的事业高度投入,但很少有人会为此献出生命。是什么区分了这些意识形态极端分子?根据本文,他们个人身份和群体身份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
方法论: 研究人员比较了两种类型的西班牙人:个人身份与国家身份“融合”或未“融合”的人。志愿者面临着经典有轨电车难题的一种自我牺牲形式的三个版本:五名西班牙人、五名欧洲同胞或五名美国人即将被失控的有轨电车撞死。但是,如果您从桥上跳下,跳到有轨电车的轨道上并死去,那么这五个人将幸免于难。在第四项研究中,他们被问到:您是否允许一名西班牙同胞跳下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杀死五名恐怖分子,或者您会推开那个人自己跳下去?
发现: 与那些身份未融合的参与者相比,身份融合的参与者更有可能牺牲自己来拯救他们的同胞。这种“道德义务”告知了身份融合的参与者决定保护欧洲人的生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扩大的群体内成员——并牺牲自己代替同胞来消灭五名恐怖分子。然而,当涉及到避免美国人或群体外人员死亡时,他们的道德信念就消失了。
启示: 令人震惊的自杀式袭击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那些声称实施此类行为的人要么是千载难逢的精神病患者,要么是被洗脑的异议人士,都忽略了导致他们进行大规模谋杀的根本心理因素。这项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启示。对于某些人来说,认同一个群体的通常过程演变成一种超越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个人的认知、情感和道德能动性完全沉浸在集体的普遍要求中。他们变得人格解体,以至于将自杀视为对其融合群体自我的自我拯救行为。
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专业人士的中心信息是,识别出此类人格并制定干预计划——通过学校和辅导员,以及在我们组织和制度结构内——旨在解除自我身份的融合或首先防止融合,可以显着降低政治或宗教殉难的风险。
6. 认识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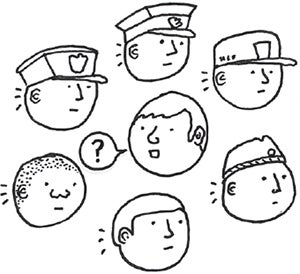
哈里·马尔特
研究:接触批评自己群体的群体外成员有助于群体间开放。 塔玛·萨古伊和埃兰·哈尔佩林(2014 年)
研究领域: 冲突解决
概述: 也许不足为奇的是,当自己群体内的成员批评我们团队的态度、信仰或行为时,我们不喜欢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是群体外成员,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这项研究表明,当我们的一位竞争对手批评自己人时,它可以显着提高我们对该群体事业的同情心。
方法论: 研究人员向以色列参与者展示了各种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虚构联合国报告。摘要在三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它们是否包含对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行为的任何批评;这种批评是由巴勒斯坦官员还是来自欧洲或中国的“外部”来源提出的;以及批评是否与冲突有关。来自巴勒斯坦人自身的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评会削弱以色列人对他们的顽固态度吗?
发现: 答案是谨慎的肯定。阅读了巴勒斯坦人自我批评的参与者——无论批评是否与冲突相关——都认为巴勒斯坦人比那些阅读了来自中国或欧洲来源的不赞成声明或那些根本没有看到批评的人更思想开放。他们变得更理解巴勒斯坦人对局势的看法,更希望找到和平解决方案,并且更愿意探索妥协的可能性。
启示: 在当前文化两极分化的氛围中,这项研究的结果与它们令人惊讶的程度一样重要。群体内谴责很可能要付出叛徒变节者的代价。但是,作为打开大门的一种手段——向警惕的群体外提供心理橄榄枝,并打破好战的、根深蒂固的信仰的防御工事——它不应被低估。伊斯兰领导人,请注意!你们公开批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犯下的恐怖暴行可以积极影响西方公众对主流伊斯兰教的看法,挑战有偏见的刻板印象。同样,美国和欧洲当局在公开辩论其外交政策的明智性时越透明,他们就越能引起对西方帝国主义动机抱有挥之不去的怀疑的穆斯林的同情。
7. 悖论式启动

哈里·马尔特
研究:悖论式思维作为促进和平的新干预途径。 博阿兹·哈梅里等人。(2014 年)
研究领域: 说服和态度改变
概述: 我们如何才能克服群体之间的历史恩怨?这项独特的纵向实地研究揭示了一种非正统的干预措施如何帮助打破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固有的僵化社会心理障碍。
方法论: 一组亲以色列支持者对照组观看了中立的以色列旅游视频。另一组人被启动以“悖论式”思考巴勒斯坦冲突:具体而言,他们观看了认可与他们自己一致但被推向极端的观点的视频。例如,这些视频表达了诸如“我们需要冲突来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类的想法。这种非理性的夸张会促使他们重新考虑他们最初的立场吗?
发现: 这项所谓的悖论式干预是在 2013 年以色列大选前进行的,它软化了参与者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它甚至影响了他们打算如何投票,增加了他们支持对实现和平感兴趣的政党的可能性。
启示: 在某些情况下,对抗极端主义哲学的有效解药可能是“看到”支持者的态度立场,然后“提高”它们。例如,为了对抗极端原教旨主义,更温和的宗教领袖可能会与个别极端分子辩论“永远不应允许妇女离开家园”的论点。这些在意识形态上一致但在实践中荒谬的错误原则的延伸可能有助于迫使人们重新评估他们的想法。
最终分析
我们描述的每项研究产生的见解都得到了充分检验的理论和额外证据的支持或反过来促成了这些理论和额外证据。因此,它们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有力视角。当然,科学理论有时会脱轨。但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行为的一些最佳工具。当寻求找到最佳前进道路时,许多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仍然将他们的信念寄托在占卜师和专栏文章或预言家的含糊不清的溢出物上,而不是科学分析,这对常识的训诫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