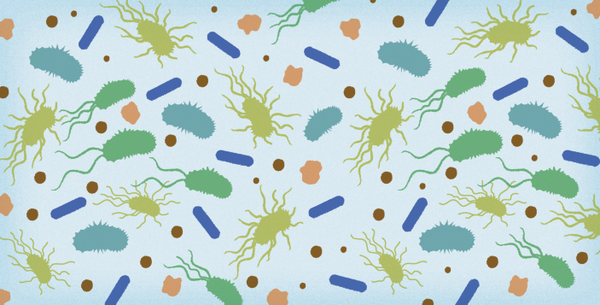在 COVID-19 冬季肆虐期间——全球确诊病例超过 9200 万例,死亡人数逼近 200 万——甚至难以想象类似的情况会在人类疾病易感性方面等待下一次机会。但这正是世界各地的健康专家必须考虑的问题,以预防或减少其他潜在的大流行病原因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思考应该已经在进行中,而且确实如此。
对已知的恐惧
未知——在这种情况下,新颖甚至难以想象的疾病——对某些人来说会产生最大的恐惧,但有很多已知的疾病类型需要担心,一些专家认为这些疾病是最危险的。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大流行病防范专家和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说:“最大的威胁仍然来自我们已经描述过的疾病。”对于全球顶级威胁,阿达利亚选择了流感病毒,他指出,流感病毒“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有能力引起大流行,而且基于其遗传结构,新的毒株迟早会出现,并具有有效的人际传播能力。”
关于支持科学新闻业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业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将帮助确保有关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致命性流感爆发有一份清单。1918-1919 年的流感大流行估计造成 5000 万 人死亡,约占世界人口的 2.5%。大约 100 万 人在 1957-1958 年的流感大流行中丧生,并且还有其他流感大流行。然而,流感并不是唯一已知的威胁。
随着 SARS-CoV-2 继续在全球许多地区肆虐,冠状病毒家族的其他成员也不应被忽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列出了 七种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但总体而言,有 数百种 冠状病毒。尽管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综合征 MERS 和 SARS 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效率不高,但阿达利亚表示,“今年的事件表明,必须比过去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个病毒家族。”例如,MERS 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大约 35% 的感染者死亡——这使其远比 COVID-19 更致命。
2018 年,阿达利亚 写道:“人类面临的最有可能自然发生的 [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 级别威胁来自呼吸道 RNA 病毒,因此这类微生物应成为防范优先事项。”他是对的,因为 SARS-CoV-2 正是这样一种病毒。现在,他甚至更广泛地认为,“任何类型的有效传播的呼吸道病毒,无论是否来自流感或冠状病毒家族,都应被视为具有潜在的大流行潜力,因为它们都具有这些相似的特征,即它们在人与人之间有效传播。”
应对耐药性
除了防御冠状病毒外,公共卫生专家还必须防御其他已知的微生物威胁,例如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AMR) 细菌。即使是现在,这些微生物每年也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约 70 万 人死亡,而耐多药结核病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专家们已经预测未来将出现更多与 AMR 相关的死亡,联合国机构间抗菌素耐药性协调小组警告说,到 2050 年,耐药性疾病可能每年导致 1000 万人死亡。
新加坡国立大学杜克医学院新兴传染病项目教授王林发表示,AMR 细菌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但他说,“至少我们可以进行系统的和有针对性的监测,这将提供一些早期预警。”
尽管人们认识到 AMR 细菌的潜在危险,但很少有制药商解决日益增长的担忧。“常见的细菌感染将继续对抗菌素产生耐药性,而且我们在制药公司的抗菌素组合方面几乎没有新的进展,”非洲科学卓越联盟的非洲重大挑战项目经理摩西·阿洛博说,该联盟总部位于肯尼亚内罗毕,是非洲科学院的 COVID-19 主席。“因此,来自我们医院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物种构成威胁。”
物种间相互作用
从非人类物种传播到人类的传染源——甚至超出冠状病毒范围的传染源——似乎也越来越危险。“有数百万种动物病毒,随着我们的人口和我们的牲畜人口增长并扩展到新的领土和生态位,这些病毒传播到人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的药物微生物学教授伊鲁卡·奥克克说。“然而,在现在到这种情况发生之间,数百万人将因现有病原体威胁而患病和/或死亡。”
许多现有的动物源性威胁造成了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例如,阿洛博指出,“病毒性出血热,如埃博拉、马尔堡、拉沙热和黄热病,可能具有潜在的危险。”其中一些感染比 SARS-CoV-2 感染更致命。平均而言, 埃博拉 病毒会杀死大约一半的感染者,但有些疫情杀死了 90% 的感染者。 马尔堡 病毒的死亡率也大致相同。
跟踪动物源性疾病也构成一个问题。对于新出现的动物源性疾病,王林发说,“我们还没有可靠且经济实惠的监测系统,因此应对措施将始终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此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监测。十多年前,科学家报告说,超过 70% 的新病原体来自动物。要领先于这些潜在威胁将很困难。
与未知因素合作
在许多方面,医疗保健系统将对致命感染保持被动反应。例如,非洲科学院高级顾问凯文·马什说,“这种威胁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无法预测下一次威胁的时间或病原体,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会有新的威胁。”因此,他说,“关键是积极监测,并建立快速识别和应对新疫情的机制。”
一个复杂的监测系统甚至可能阻止另一种疾病如此快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需要建立适当的微生物监测网络,以监测各区域内感染的任何发展——基本上要有一个病原体遗传监测小组,专注于这些活动,”阿洛博说。“需要早期预警系统。”
预警系统会有所帮助。然而,面对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医疗保健系统不能等到疫情爆发才做出反应。
科学与社会相遇
也许与任何其他事情一样,公众对 COVID-19 的一些反应让专家感到惊讶。一年前,奥克克认为,新兴微生物威胁的最大挑战将来自检测它和开发疫苗。现在,在观察了对 COVID-19 的反应后,她说,最大的挑战“将是说服人们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保护人类免受威胁。”尽管在检测 SARS-CoV-2 和开发几种有效疫苗方面取得了快速成功,但奥克克说,“在大多数国家,让人们待在家里或戴口罩以避免传播是不可能的。”她补充说,“当在跳过假期和对他人生命构成致命风险之间做出选择时,有足够多的人选择了后者,我们不得不假设他们会再次这样做。”因此,准备工作超越了科学,深入到世界各地的社会。
弄清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将取决于多种形式的研究。例如,奥克克说,“我希望看到一些政治、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以便公共卫生部门能够更好地了解如何说服或劝说人们在疫情中做出拯救生命的决定。”
改进政策决策的需求不仅限于公民或医院。正如王林发所讨论的那样,“真正的改变将来自于政策和法律框架的改变,即在透明和高效地报告‘异常病例’的背景下,以及一个尽可能远离地缘政治的统一国际大流行病防范体系。”
与此同时,应该追求更多的基础科学。在这里,奥克克建议更多地研究传染病生物学,包括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和疫苗开发。此类研究可以帮助科学家预测下一个重大威胁及其最可能的来源,甚至“比 COVID-19 的创纪录时间更快地阻止它,并更快地做出反应,”奥克克解释说。
采取持续的视角
公共卫生专家知道,人们总是面临着严重的传染病问题,而不是关注全球健康领域最大的灾难,例如 1918 年的流感和当前的 COVID-19 大流行。随着对全球持续研究的投资,可能会产生许多好处。“除了避免下一次公共卫生灾难外,这也将有可能解决困扰我们几个世纪的流行病威胁,并且如果没有协调一致地推动发现和行动,这些威胁将继续存在,”奥克克说。
世界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微生物威胁,但研究与技术相结合可以大大降低疾病失控的几率。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尽可能地领先于这些疾病。
本文经许可转载,最初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在 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