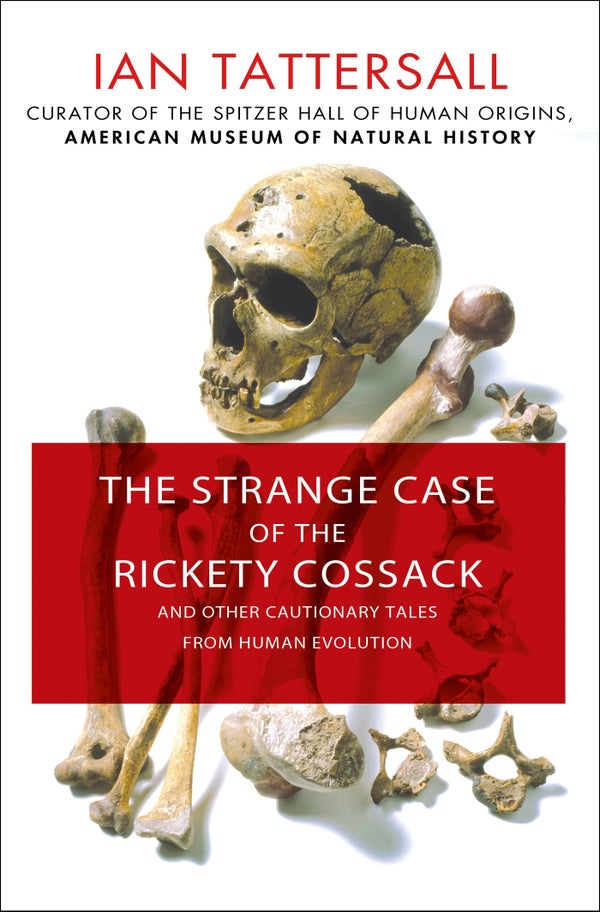摘自《摇摇晃晃的哥萨克人的怪异案例,以及人类进化中的其他警示故事》,作者:伊恩·塔特索尔。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5年。版权所有©2015年。经许可转载。(《大众科学》是麦克米伦出版社的一部分。)
如果我必须选择二十世纪古人类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1950 年。当然,狄奥多西·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早在 1944 年就将综合进化论引入了古人类学领域,但当时正值战时,似乎没有人立即注意到。尽管如此,多布赞斯基对人类进化的看法指向了未来,在许多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就是他的文章发表后的那一年,也标志着古人类学领域旧卫队的没落。1948 年,年迈但仍然勤奋的亚瑟·基思(Arthur Keith)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类进化新理论》的书,但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有兑现其标题。如果说它还被人记住的话,也是因为它含糊的反犹太立场。现在是新一代人物登上古人类学舞台的时候了。
新一代生物人类学家中的领军人物是舍伍德·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沃什伯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哈佛接受了相当传统的培训,在 1940 年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后,他热情地拥抱了新进化综合论。正是通过这位精力充沛的皈依者,综合进化论最终得以进入古人类学领域。1950 年,沃什伯恩(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和多布赞斯基共同组织了一场由长岛冷泉港实验室主办的会议。这次国际会议以“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为宏大主题,汇集了包括综合进化论的三位巨头在内的众多古人类学和相关科学领域的知名人士。因此,会议星光熠熠,但事后看来,其中一个贡献不仅是会议上最受关注的演讲,也是古人类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基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由古人类学家提出的。它是由鸟类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提出的。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塑造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迈尔在印刷版上和在演讲中一样有力——尽管他的出版版本带有匆忙准备的所有痕迹——他毫不客气地直言不讳。他毫不含糊地告知在场的大多数人,所有那些人族物种和属所暗示的人类进化复杂图景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他宣称,解剖学家区分它们的理论和形态标准都是完全不合适的。例如,如果你将一对果蝇物种放大到人类大小,它们看起来会比任何一对活着的灵长类动物的成员彼此之间的差异更大。化石人族的情况也是如此。
虽然这个比喻非常不相关,但它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他们不安地意识到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薄弱。它让观众为迈尔更具体的说法做好了准备,即所谓的人族属和物种的多样性根本不存在。迈尔继续说,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原则上,这种多样性也不可能存在,因为物质文化的存在如此显着地扩大了使用工具的人族的生态位,以至于世界上永远不可能同时容纳不止一种人类物种。
迈尔说,总而言之,这些各种实际的和理论的考虑因素决定了,所有已知的人类化石都应该被归入一个单一的、不断进化的多型谱系。而且,在这个谱系中,只有三个物种可以识别,而且每个物种都属于一个属:人属。正如迈尔所认为的那样,南方古猿(南方古猿)产生了直立人(包括爪哇猿人、北京猿人等等),而直立人又进化成了智人(包括尼安德特人)。事情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似乎他总觉得事情不可能如此简单——迈尔明确询问,为什么与几乎任何其他成功的哺乳动物科不同,人科没有产生一系列物种。“是什么,”他问道,“导致人族停止物种形成,尽管它在进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功?”他对这个优秀问题的巧妙回答,又让他回到了“人类巨大的生态多样性”。迈尔宣称,人类已经“专注于非专业化”。更重要的是,“人类占据的生态位比任何已知的动物都多。如果单一物种的人类占据了所有为类似人属生物开放的生态位,那么很明显,他不能物种形成”(我的重点)。迈尔还注意到关于“人类”的另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至少在他看来,这支持了他对人类系统发育的重构,即今天的无处不在的智人无限地倒退回过去:“人类显然特别不能容忍竞争者……入侵的克罗马农人消灭尼安德特人只是一个例子。”
迈尔在他的演讲结束时接受了提问。当被问到(当然不是古人类学家)化石人族之间发现的显着形态差异如何才能被压缩到一个属中时,他巧妙地回答说,“由于没有绝对的属特征,因此不可能在纯粹的形态学基础上定义和划分属。”当时没有人觉得应该对此提出质疑。没有人指出显而易见的事实:形态学是古生物学家唯一可以使用的东西,而且,虽然他可能在技术上正确地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属特征”——无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化石属必须从它们的形态学中识别出来。也没有人认为,不能容忍竞争可能仅仅是智人的一个特征,使其与即使是最亲近的亲戚区分开来。也没有人质疑迈尔的其他任何广泛而高度推测性的声明——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他具有挑衅性的评论发表后的几年里。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如此顺从地接受他对该领域的各种批评的原因是,迈尔的猛烈抨击使古人类学家中极少数的精英人士陷入了某种早就应该进行的内省。他们最终开始意识到,他们及其前辈一直在一个理论真空状态下运作,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人——或许除了弗兰茨·魏登赖希(Franz Weidenreich)——曾费心思考过可能支持他们关于化石的故事的进程,或者他们的运作假设如何与已知的大自然其他部分是如何进化的相适应。而迈尔,这位自我肯定的综合进化论的架构师,对他们的科学进行了雄辩而全面的分析:该分析将对形态学的认可与对进化过程、系统学、物种形成理论和生态学的考虑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关键因素都是古人类学家现在开始感到内疚地基本上忽略的——从而产生了关于人类进化的连贯而有力的论述。在没有思想退路的情况下,他们除了屈服还能做什么?在这种令人不安的认识论境况中,几乎没有人介意迈尔的设想远非牢固地扎根于化石本身的研究中。
对这种瞬间投降的主要英语国家例外是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room)的年轻助手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他详细指出,纤细型和粗壮型南方古猿之间的形态异质性——以及他看到的一些南非和早期爪哇材料之间的一些相似性——表明,在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至少存在两个共存的人族谱系。尽管迈尔勉强承认罗宾逊确实有道理,但这一承认被埋藏在一份古人类学家不读的期刊上发表的一堆注释中,一旦罗宾逊指出了这一点,他的大多数同事都同意,粗壮型南方古猿最好被排除在迈尔的线性方案之外。属名南方古猿继续用于所有纤细型南方古猿(对一些古人类学家,主要是罗宾逊来说,粗壮分支继续被称为傍人属)。罗宾逊自己也继续使用“汤加普人”(他的引号)这个名字来称呼来自斯沃特克兰斯(Swartkrans)的神秘、非常轻巧的人族化石——以及从斯泰克方丹(Sterkfontein)的一个区域来的,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该区域也开始生产一些粗糙的石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