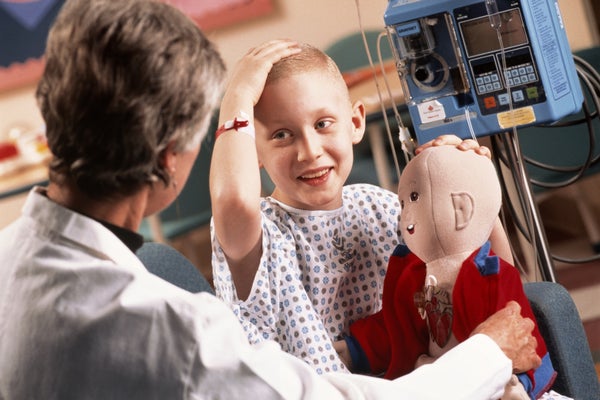九年前的一个星期一下午,密歇根州德威特市一位牧师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母亲桑德拉·史密斯得知自己患有侵袭性乳腺癌。然而,真正糟糕的消息会在当周晚些时候打击这个家庭。
起初他们以为他们最小的六岁儿子安德鲁只是得了流感。然后他开始呕吐。他还出现了面部下垂,步态似乎也不稳。史密斯回忆说,即使他们冲到急诊室,她还在想他们是否“小题大做”了。
事实远非如此。MRI 扫描显示安德鲁的脑干中有一大片肿胀区域——清楚地表明他患有一种致命的儿童癌症,这种癌症通常在四到十岁之间发病,并且大多数患者在确诊后一年内死亡。与史密斯乳房中不受控制分裂的细胞不同,她儿子的癌症,称为弥漫性内生性脑桥神经胶质瘤 (DIPG),无法通过手术或传统化疗来对抗。在 DIPG 中,恶性细胞与控制呼吸和心率等关键功能的区域中的正常脑组织缠绕在一起,使得外科医生无法切除。在 200 多项药物试验中,没有任何方法比放射疗法更有效,而放射疗法本身只能将 DIPG 儿童的生命延长几个月。安德鲁比“典型”的 DIPG 患者活得更久,在确诊后两年多后去世,于 2009 年底去世。
关于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DIPG 约占儿童脑部和脊髓肿瘤的 10%。它是第二常见的儿童脑肿瘤,也是儿童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DIPG 的治疗方案和生存率在 40 年内没有改变——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报告,这种困境可能促使脑癌超越白血病成为美国最致命的儿童恶性肿瘤。
然而,今天,由于基因测序方法的进步以及安德鲁等因这些疾病失去孩子的家庭捐赠的肿瘤组织,DIPG 和其他儿童脑癌的前景看起来更加光明。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利用患者的肿瘤组织生成了数十种细胞系和小鼠模型,以研究儿童脑癌的基础生物学。时机已经成熟。在精准医学的曙光中,精准医学旨在为个体患者定制疾病治疗,遗传学和基础科学发现表明,为什么过去的试验可能会失败,并正在指导未来和正在进行的努力,以确定针对这些毁灭性疾病的有效疗法。
米歇尔·蒙杰是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病学助理教授,她大约在 2002 年作为那里的医学博士/博士生首次接触到 DIPG。蒙杰说,她与她的临床导师一起照顾一位因 DIPG 而濒临死亡的九岁女孩,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种我们不知道如何治疗的疾病”。“我感觉与这位患者非常亲近,并且因自己无能为力而感到沮丧。”
那时,关于 DIPG 的分子数据很少。没有动物模型。没有细胞培养物。生成此类研究工具需要患者的肿瘤样本。然而,由于 MRI 扫描可以可靠地诊断典型的 DIPG,并且获取脑干组织并非易事,因此很少进行活检。蒙杰说,由于实验室中可供研究的肿瘤组织非常少,DIPG 的研究进展停滞了几十年。
2007 年,法国的一个外科医生团队报告称,他们使用立体定向技术安全地从 24 名 DIPG 儿童身上获取了活检样本,该技术使用计算机成像来引导针头放置。这项研究激发了达纳-法伯/波士顿儿童癌症和血液疾病中心脑肿瘤中心临床主任、儿科神经肿瘤学家马克·基兰长期以来的努力,他多年来一直在美国推动 DIPG 活检,但最初没有成功。
那时,技术进步使得从微小的组织碎片中读取 DNA 序列成为可能,这进一步推动了现在已证明在训练有素的人手中是安全的一项棘手的外科手术。波士顿团队开始为患者提供在诊断和复发时活检的肿瘤的基因组测序,以“了解肿瘤是如何进化的,并将适当的药物重新定向到肿瘤”,基兰说。肿瘤图谱可以帮助确定哪些患者可能从一种称为靶向疗法的新型药物中获益,这种疗法靶向肿瘤中的特定蛋白质,而不仅仅是杀死任何分裂的细胞。靶向疗法是精准医学的基石。
自 2009 年以来,达纳-法伯的研究人员对近 1,000 名儿童的脑肿瘤进行了测序。在被归类为低级别神经胶质瘤的儿童中,高达 10% 的儿童在一种名为BRAF的基因中发生突变,这种突变在某些成人皮肤肿瘤中也可见。几年前,来自欧洲和北美的 32 名患有BRAF阳性神经胶质瘤的儿童参加了一项达拉非尼临床试验,达拉非尼是一种靶向疗法,已获准用于患有这种突变的黑色素瘤患者。在本月早些时候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基兰报告称,32 名儿童中有 23 名在使用 BRAF 抑制药物后病情有所改善——这种反应率非常高,以至于他的团队正在为携带这种突变的试验参与者提供持续治疗。
2012 年,基兰和合作者启动了一项临床试验,对 DIPG 儿童的肿瘤进行活检,检测几种分子标记物,并根据结果分配四种治疗策略之一。两年前,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儿科神经肿瘤学家萨宾·穆勒领导的团队启动了另一项 DIPG 试验。这项研究使用更复杂的技术,全外显子组测序来探测患者的肿瘤,该技术扫描基因组的整个蛋白质编码部分,而不仅仅是检查预先指定的标记物。根据每位患者的肿瘤图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团队提出了多达四种似乎合适的药物。还需要一到两年才能看到这些药物是否有帮助。
尽管精准医学对某些个体有帮助,但它很昂贵,一些科学家怀疑它可能只会适度改善一般癌症患者的生活。单个肿瘤内的细胞可以获得不同的突变,因此,“即使存在有效的药物,它也可能益处有限,因为在肿瘤其他部分活跃的分子通路将导致来自不同肿瘤细胞克隆的肿瘤生长,”研究人员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9 月份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并且在没有针对 DIPG 的特定批准药物的情况下,关于活检是否为这些患者提供真正益处的争论仍在继续。
一些实验室采取了一种争议较少的 DIPG 样本获取途径——从同意在孩子去世后捐赠肿瘤组织的家庭那里获得遗赠。密歇根州的母亲史密斯在 2008 年春天通过一个在线 DIPG 支持小组了解了遗赠,那是她的儿子安德鲁被诊断出患病半年后。史密斯回忆说,阅读到死后取出大脑并捐赠组织的帖子“对我来说太可怕了”。“但我明白[如果没有患者样本],研究人员就无法研究这种肿瘤。”她在她和她的朋友主持的一个 DIPG 家庭雅虎群组中分享了这个想法。2008 年 11 月,雅虎列表中的一位母亲惊慌失措地打电话给史密斯。她的女儿已进入弥留之际,家人想捐赠她的肿瘤组织,但尚未做出安排。
尸检组织捐赠在后勤方面具有挑战性。一旦孩子去世,需要在六小时内取出大脑,并将肿瘤组织放入无菌管中。然而,患者往往死在家中,远离医疗中心,有时在半夜或节假日期间的暴风雪中。一些实验室从靠近孩子居住地的组织回收团队预订随叫随到服务。为了产生最大的影响,样本应该送到可以在同一天接收和处理它们的实验室。
在史密斯帮助其他家庭安排肿瘤捐赠的过程中,她结识了一些顶尖的 DIPG 研究人员,包括蒙杰,蒙杰刚刚研究出一种方法培养尸检组织中的细胞,并使用这些细胞创建 DIPG 小鼠模型。2011 年 7 月,史密斯得知一位名叫麦肯纳的七岁女孩正在与 DIPG 作斗争。蒙杰和史密斯与这个家庭合作,“确保我们在时机到来时拥有所需的文件”,麦肯纳的母亲克里斯汀·韦策尔说,她是一位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的高中教师。
麦肯纳突然衰弱,家人决定在她去世后一小时内捐赠她的肿瘤组织。韦策尔说,尽管很痛苦,但这个决定“出乎意料地令人欣慰”。“这是一种反击偷走我们女儿的怪物的方式。”韦策尔一家此后帮助其他 DIPG 家庭进行肿瘤捐赠,并创建了一个基金会,以提高人们对儿童脑癌的认识并资助相关研究。该基金会支付向蒙杰实验室捐赠组织的费用,并为一名技术人员支付工资,该技术人员维护实验室的 DIPG 培养物,并将样本运送到世界各地约 80 个实验室。蒙杰说,支持力度各不相同,但通常约为每年 10 万美元。
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神经生物学和脑肿瘤项目负责人之一的神经生物学家苏珊娜·贝克说,尸检组织捐赠“将研究领域从一个由于缺乏研究材料而难以接近的问题,转变为对 DIPG 基因组进行前所未有的分析”。
贝克、基兰以及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和其他地方的其他研究人员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尽管 DIPG 具有与其他脑癌不同的基因特征,但这种罕见的儿童肿瘤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几乎80% 的肿瘤在编码一种名为组蛋白 H3 的蛋白质的基因中发生突变。组蛋白就像 DNA 缠绕在其上的线轴。组蛋白是表观遗传学——研究基因开启或关闭的生物学机制——的关键参与者,它会影响酶访问 DNA 的容易程度,这些酶将遗传密码翻译成工作蛋白质。“组蛋白 H3 非常基础……我认为许多癌症都会发生这些突变,”贝克说。然而,它们似乎是 DIPG 和儿童中约三分之一的非脑干肿瘤所独有的。
这些基因洞见来得正是时候。当一些实验室忙于分析 DIPG 肿瘤细胞的全基因组测序数据时,另一些实验室则在细胞培养物和小鼠模型中测试潜在药物,这些细胞培养物和小鼠模型是从患者脑肿瘤样本中生成的。其想法是在实验室中仔细审查化合物,然后再选择哪些化合物进行时间更长、成本更高的临床试验。这种方法并非革命性的。蒙杰说,一般来说,这是“你进行医学研究的方式”。但对于 DIPG 来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一直没有细胞培养物或模拟该疾病的实验小鼠。
情况在 2010 年有所改善,当时时任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查尔斯·凯勒组织了一项全球筛选工作。那时,许多实验室正在从 DIPG 肿瘤组织中创建细胞培养物。作为提议用于 DIPG 临床试验的药物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凯勒召集了蒙杰实验室和其他 12 个小组,汇集资源进行合作研究。他的小组将 83 种潜在药物分配到孔板上,并将它们送到其他实验室进行测试。在这些遥远的实验室中,研究人员将孔板装载 DIPG 细胞培养物,并寻找变成蓝色的孔——这是一种化学指示,表明该药物正在杀死肿瘤细胞。顶级候选药物也提高了植入 DIPG 肿瘤的小鼠的存活率。
此外,这些实验室还从其 DIPG 细胞系中纯化了遗传物质,并将 DNA 和 RNA 样本送到俄勒冈州进行测序,以建立细胞基因故障与药物反应之间的明确联系。凯勒说,检查这些联系至关重要,因为许多基于 DIPG 细胞突变看起来很有希望的药物在细胞分析中没有显示出任何效果。
但出现了一个赢家——一种名为帕比司他的药物,它可以抑制化学修饰组蛋白的酶。巧合的是,当全球筛选手稿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帕比司他作为另一种癌症(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药物。这些结果帮助启动了一项帕比司他的临床试验,该试验于 5 月开始招募患者。这项由蒙杰领导的试验将测量副作用,并确定治疗 DIPG 儿童的最佳药物剂量。然而,帕比司他不会成为灵丹妙药。实验室数据显示,一些 DIPG 细胞对该药物产生耐药性,这表明它需要与其他疗法联合使用才能在患者中获得生存益处,蒙杰说。
帕比司他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许多脑癌疗法共同面临的挑战——有效地将它们输送到大脑中。“许多药物无法穿过血脑屏障,因此它们无法到达肿瘤,”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穆勒说。一些研究人员正在使用一种称为对流增强递送的程序,通过细小的导管将药物直接输送到脑肿瘤中。另一些研究人员正在使用纳米技术来重新配制药物,使其更具特异性和持久性——例如,通过插入分子标签,将药物定向到肿瘤上唯一发现的分子。穆勒说,DIPG 的好药可能已经存在,但“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输送它们。”她正在计划未来一项在 DIPG 儿童中使用对流增强递送帕比司他的试验。
与此同时,蒙杰的实验室和其他小组正在使用表观遗传剂和联合方案进行额外的药物筛选,凯勒创立了一家非营利性癌症生物技术公司,以加速候选药物从基础科学研究到临床试验的转移。每年,他的团队都会组织一个为期一周的速成课程,向家庭介绍儿童脑癌,并解释肿瘤组织捐赠如何推动研究。
一些家庭定期访问实验室,在显微镜下观察孩子的细胞。韦策尔一家在女儿因 DIPG 去世八到九个月后访问了蒙杰的实验室。“当我第一次看到麦肯纳的细胞时,我开始无法控制地哭泣,”韦策尔说。“我想拿起每一个培养皿……然后把它扔到墙上,摧毁细胞系,就像它摧毁了我的女儿一样。”
现在,在每年大约一次的实验室访问之后,韦策尔的感觉有所不同。“我把它看作是麦肯纳的最后一战……她给世界和她之后的孩子们的礼物。如果麦肯纳不能留在这里,就让她以她现在唯一能做的方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有助于我们认为她的死是有一些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