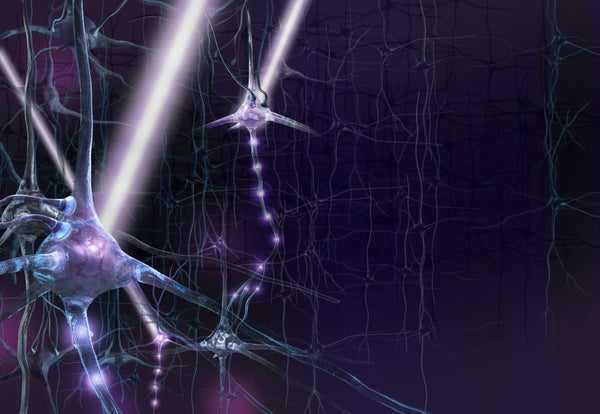关于支持科学新闻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将帮助确保有关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尽管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我们对精神疾病(全球因死亡或残疾而导致生命年损失的主要原因)的有限了解阻碍了对治疗方法的探索,并导致了污名化。显然,我们需要精神病学的新答案。但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可能说过的那样,在我们找到答案之前,我们需要提出新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新技术。
然而,开发适当的技术是困难的,因为哺乳动物的大脑在复杂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其中数百亿个相互交织的神经元——具有无数不同的特征和布线模式——通过精确计时的毫秒级电信号以及丰富的生物化学信使进行计算。由于这种复杂性,神经科学家对大脑的真正运作方式——特定脑细胞内的特定活动模式如何最终产生思想、感觉和记忆——缺乏深入的了解。由此推论,我们也不知道大脑的物理故障如何产生不同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精神疾病的统治范式——将其定义为化学失衡和神经递质水平的改变——并不能充分解释大脑的高速电神经回路。而且精神疾病的治疗在历史上大多是偶然的:对许多人有帮助,但很少有启发作用,并且面临着与基础神经科学相同的挑战。
在1979年《大众科学》的一篇文章中,诺贝尔奖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is Crick) 认为,神经科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需要控制大脑中的一种细胞,同时保持其他细胞不变。电刺激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因为电极是一种过于粗糙的工具:它们会刺激其插入部位的所有电路,而不区分不同的细胞类型,而且它们的信号无法精确地关闭神经元。药物的特异性也不够,而且它们的速度比大脑的自然运行速度慢得多。克里克后来在演讲中推测,光可能具有作为控制工具的特性,因为它可以用精确计时的脉冲传递,但当时没有人制定使特定细胞对光敏感的策略。
与此同时,在生物学的一个领域中,与哺乳动物大脑的研究相距甚远,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微生物,而这些微生物直到很久以后才被证明是相关的。至少在 40 年前,生物学家就知道,一些微生物会产生蛋白质,这些蛋白质直接调节细胞膜上的电荷流动,以响应可见光。这些蛋白质由一组特征性的“视蛋白”基因产生,有助于从微生物环境中的光中提取能量和信息。1971 年,当时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沃尔特·施托克纽斯 (Walther Stoeckenius) 和迪特·奥斯特海尔特 (Dieter Oesterhelt) 发现,其中一种蛋白质细菌视紫红质充当单组分离子泵,可以被绿光的光子短暂激活——一种卓越的多功能分子机器。后来对该蛋白质家族的其他成员——1977 年的盐视紫红质和 2002 年的通道视紫红质——的鉴定延续了 1971 年的最初主题,即单基因、多功能控制。
事后看来,克里克挑战的解决方案——一种可能大大推进大脑研究的潜在策略——早在他在提出挑战之前就已经潜伏在科学文献中。然而,直到 2005 年夏天,这些领域才在新技术(光遗传学)中融合,该技术基于微生物视蛋白基因,这花费了 30 多年的时间。
光遗传学是遗传学和光学技术的结合,旨在控制活组织特定细胞内定义明确的事件。它包括发现和将赋予光响应性的基因插入细胞;它还包括将光深入输送到像自由移动的哺乳动物一样复杂的生物体中的相关技术,将光敏感性靶向感兴趣的细胞,以及评估这种光学控制的特定读数或效果。
光遗传学让神经科学家兴奋的是,它能够控制特定细胞类型在特定时间内发生的特定事件——这种精确程度对于生物学的理解至关重要,甚至超越了神经科学。细胞中任何事件的意义只有在组织的其他部分、整个生物体甚至更大环境中发生的其他事件的背景下才具有完全的意义。例如,神经元放电时间即使仅移动几毫秒,有时也会完全逆转其信号对神经系统其他部分的影响。而且,在行为哺乳动物中,毫秒级的时间精度对于深入了解正常大脑功能以及帕金森病等临床问题至关重要。
光遗传学、医学和精神病学
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表明,精神疾病是全球因死亡或残疾而导致生命年损失的主要致残原因。即使是单一的精神疾病,即重度抑郁症,也是全球 15 至 44 岁女性致残的主要原因。但仍然存在很多污名(这可能与为什么听到这种流行病学对许多人来说如此令人惊讶有关)。为什么有污名?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集体缺乏理解。正如癌症的诊断曾经比现在带有更多的污名一样(也许是因为对癌症的真正“本质”感到困惑、对传染病的担忧,甚至是因为将癌症归咎于患者的人格特征),对精神疾病缺乏深入了解也会导致污名化,从而进一步减缓在全球人类健康这一巨大问题上的进展。可悲的是,这种缺乏深入了解是普遍存在的:在全球范围内,从普通大众到最有影响力和最先进的精神科医生,我们都不知道精神疾病在根本上的“本质”。
举一个例子:什么是抑郁症?例如,与心力衰竭的情况不同,我们没有很好的模型来解释抑郁症代表哪种器官功能障碍。心脏是一个泵,其功能障碍(作为一阶近似)与其泵血有关,这是可以很容易理解、测量、建模和调整的。但是,我们对大脑的真正运作方式缺乏深入了解,这当然意味着我们不了解其故障模式。
我不断地面对这个挑战。除了在生物工程系运营一个研究实验室外,我还是一名执业精神科医生,我定期使用药物、治疗和电或磁脑刺激的组合来治疗患者。在哈佛大学完成本科学习后,我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和博士学位,专注于突触电生理学和哺乳动物神经回路的光学研究。然后,我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实习期和博士后研究,在那里我成为一名医生,并培养了动物行为研究的技能。虽然作为一名医生,我使用了现代工具(如经颅磁刺激),但这些工具仍然不够好,最重要的是,它们没有提供对疾病的深入了解,而只是突出了(正如患者一样)我们的局限性。我记得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大学生患有精神病性抑郁症,他被脑海中难以理解的声音和无法控制的奇异想法吓坏了。我记得一位退休妇女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以至于她无法微笑,几乎无法进食,并且对她的孙子孙女没有反应。我无法以科学的方式解释这些变化,以及这些患者经历的治疗不幸失败,这些经历从未离开我的脑海。
作为 2004 年在斯坦福大学的首席研究员和精神科医生(并得到了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新拨款的支持),我得以组建并启动一个研究团队,以解决精确神经控制的技术挑战。而且,正如科学界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们对新想法的集体需求帮助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被要求反思我们在这里的光遗传学工作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考虑科学过程的更广泛意义。
照亮生命
生物学具有利用光来干预生物系统的传统。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使用一种名为 CALI 的光基方法来破坏并因此抑制选定的蛋白质;例如,激光也已被用来破坏线虫 Caenorhabditis elegans 中的特定细胞。相反,贝尔实验室的理查德·L·福克(Richard L. Fork,在 1970 年代)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拉斐尔·尤斯特(Rafael Yuste,在 2002 年)报道了用激光刺激部分破坏细胞膜的神经元的方法。最近,当时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格罗·米森伯克 (Gero Miesenböck) 以及当时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埃胡德·伊萨科夫 (Ehud Isacoff)、理查德·H·克莱默 (Richard H. Kramer) 和德克·特劳纳 (Dirk Trauner) 的实验室采用了多组分系统来利用光调节靶向细胞。例如,他们引入了一种调节神经元的蛋白质和一种在紫外光触发时会刺激蛋白质起作用的化学物质。
然而,破坏感兴趣的蛋白质或细胞显然会限制实验选择;虽然优雅且有用,但依赖多个组件的方法会带来实际挑战,并且在哺乳动物中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或效用。有必要从根本上转向单组分策略。事实证明,这种单组分策略无法建立在早期方法的任何部分或方法之上,而是采用了来自微生物的卓越多功能光激活蛋白质:现在称为细菌视紫红质、盐视紫红质和通道视紫红质的蛋白质。
在细菌视紫红质和嗜盐菌视紫红质被科学界认识之后,2000年,日本的 Kazusa DNA 研究所在线发布了来自莱茵衣藻 (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 的数千个新的基因序列。当时在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 Peter Hegemann 在审阅这些序列时,注意到有两个与细菌视紫红质相似的长序列,他曾预测莱茵衣藻会有一个光激活离子通道。他从 Kazusa 获取了这些序列的副本,并请 Georg Nagel(当时在法兰克福的一位首席研究员)测试它们是否确实编码离子通道。2002 年,Hegemann 和 Nagel 描述了他们的发现,其中一个序列编码了一个对蓝光敏感的单蛋白膜通道:当被蓝色光子击中时,它会调节带正电离子的流动。因此,该蛋白质被命名为通道视紫红质-1,或 ChR1。次年,Nagel 和 Hegemann(以及他们的同事,包括法兰克福的 Ernst Bamberg)探索了另一个序列,并将编码的蛋白质命名为“通道视紫红质-2”,或 ChR2。几乎与此同时,休斯顿的 John L. Spudich 提供了证据,表明这些基因对于莱茵衣藻的光依赖性反应很重要。但是,这些通道视紫红质——第三种单组分光激活离子传导蛋白——并没有像前几十年发现的细菌视紫红质和嗜盐菌视紫红质那样立即转化为神经科学的进步。自从 1971 年以来,2002 年之后又平静地过去了几年。
许多科学家向我透露,他们曾考虑将细菌或藻类视蛋白基因插入神经元,并尝试用光来控制改变后的细胞,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诚然,在生物学中一切皆有可能,但实际上能够实现又是另一回事。由于资金挑战、支持受训人员职业生涯的低风险项目需求以及其他问题,现代学术科学对风险承担的门槛非常高。动物细胞不太可能有效或安全地制造这些微生物膜蛋白,而且这些蛋白质几乎肯定会太慢太弱而无法发挥作用。此外,要发挥作用,这些蛋白质还需要一种额外的辅助因子——一种称为全反式视黄醛的维生素 A 相关化合物来吸收光子。浪费时间和金钱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尽管如此,对于我在斯坦福大学组建的生物工程研究团队来说,提高我们对精神疾病状态下大脑的理解的动力足以证明极高的失败风险是合理的。作为 2004 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的首席研究员,我组建了一个团队,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研究生 Edward Boyden 和 Feng Zhang(他们现在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来应对这一挑战。我通过成熟的转染技术,将通道视紫红质-2 引入培养的哺乳动物神经元中——即将 ChR2 的基因和一种特定的开关或启动子剪接到一个载体(如良性病毒)中,该载体将添加的遗传物质运送到细胞中。启动子可以确保只有选定的神经元类型(例如那些能够分泌神经递质谷氨酸的神经元)会表达或制造编码的蛋白质。
出乎意料的是,实验效果惊人地好。我们仅使用安全的可见光脉冲,就实现了对细胞动作电位发放模式的可靠、毫秒级精确控制——动作电位是电压突变或脉冲,使一个神经元能够向另一个神经元传递信息。2005 年 8 月,我的团队发表了第一份报告,表明通过引入微生物视蛋白基因,我们可以使神经元精确地对光作出反应。通道视紫红质(以及我们最终发现的,1971 年的细菌视紫红质和嗜盐菌视紫红质)都被证明能够有效地、安全地响应光而打开或关闭神经元。它们起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哺乳动物组织中天然含有大量的全反式视黄醛——光子激活微生物视蛋白所必需的一种化学辅助因子——因此除了视蛋白基因之外,无需向目标神经元添加任何东西。微生物视蛋白基因为长期寻求的单组分策略提供了途径。改善自然
自那以后,由于生态学和工程学的显著融合,光遗传工具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功能多样性迅速扩展。研究人员通过在自然界中搜寻新的视蛋白来将其添加到工具包中;他们还应用分子工程来调整已知的视蛋白,使其在更广泛的生物体中对不同的实验更有用。
例如,在 2008 年,我们由 Feng Zhang 领导的对不同藻类物种 — 卡特氏沃尔沃克斯 (Volvox carteri) 的基因组搜索发现了一种第三种通道视紫红质 (VChR1),正如我们与 Peter Hegemann 一起展示的那样,它对黄光而不是蓝光做出反应。通过同时使用 VChR1 和其他通道视紫红质,我们可以同时控制混合的细胞群,黄光对其中一些细胞施加一种类型的控制,而蓝光则向另一些细胞发送不同的命令。我们现在发现,最有效的通道视紫红质实际上是 VChR1 和 ChR1 的混合体(完全没有 ChR2 的贡献)。我们其他修改过的视蛋白(与 Ofer Yizhar、Lief Fenno、Lisa Gunaydin 以及 Hegemann 和他的学生一起创建)现在包括“快”和“慢”通道视紫红质突变体,它们可以精确控制动作电位的时间和持续时间:前者可以以每秒 200 次以上的速度驱动动作电位,而后者可以通过单次光脉冲将细胞推入或推出稳定的兴奋状态。我们最新的视蛋白现在也可以响应接近红外线的深红光,这种光线聚焦更清晰,更容易穿透组织,并且受试者非常耐受。现在,许多小组也在推进视蛋白工程,包括日本的 Hiromu Yawo、法兰克福的 Ernst Bamberg 和圣地亚哥的 Roger Tsien 的小组。
现在在各种非动物基因组中发现的许多天然视蛋白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哺乳动物细胞无法很好地制造。但是,我小组中的 Viviana Gradinaru 开发了许多通用策略来改进它们的传递和表达。例如,“运输”DNA 片段可以与视蛋白基因捆绑在一起,充当“邮政编码”,以确保基因被运输到哺乳动物细胞内的正确隔室,并正确翻译成功能蛋白质。这种通用的方法有助于解锁微生物视蛋白基因的广泛生态资源。
分子工程还将光遗传控制扩展到细胞的电行为之外,扩展到明确的生化事件。所有获得批准的医疗药物中有很大一部分作用于一类称为 G 蛋白偶联受体的膜蛋白。这些蛋白质会感知细胞外信号化学物质,例如肾上腺素,并通过改变细胞内生化信号(如钙离子)的水平以及细胞的活性来做出反应。通过将来自视紫红质分子的光敏域添加到 G 蛋白偶联受体中,2009 年初,Raag Airan 和我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发表了一组称为 optoXRs 的受体,它们对绿光快速反应。当使用病毒将单组分 optoXR 基因插入实验室啮齿动物的大脑中时,实现了对定义的生化途径的第一个细胞类型特异性快速光学控制,甚至可以在自由移动的哺乳动物中工作。现在,许多实验室也在探索对定义的生化事件的光学控制,这为生物学中几乎每个细胞和组织的光遗传学打开了大门。
借助我们在 2006 年和 2007 年开发并发布的纤维光学工具,研究人员现在可以将光传递到大脑的任何区域(无论是表面还是深层),以在自由移动的哺乳动物中进行光遗传控制。为了实现对光遗传控制引发的动态电信号的同步读数,我们还发布了毫秒级的仪器,这些仪器是光纤和电极的集成混合体(“光电极”)。光学刺激和电记录之间可以产生长期的协同作用,因为可以将两者设置为互不干扰。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同时直接观察参与运动控制的神经回路中不断变化的电活动,同时我们正在使用微生物视蛋白光学控制这些回路。我们的光遗传输入和神经回路的电输出测量越丰富和复杂,我们就能越有力地推断神经回路的计算和信息作用,以及它们如何转换我们的信号。
重返精神病学
光遗传学作为一种研究工具的重要性,特别是与其他技术结合使用时,继续快速增长。除了向全球 700 多个实验室分发这些不同的工程视蛋白基因 ( http://www.optogenetics.org ) 之外,我的学生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努力开发和提供光遗传学指导。我们发现,尽管光遗传学需要不寻常的技术组合,但基本原理可以在实验室的重点实践课程中教授,这加快了该技术的好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前来实践光遗传学并返回其所在机构,他们在那里充当当地知识和智慧的来源,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同环境和挑战中得到应用。
一个意想不到的应用示例涉及脑成像。近年来,神经科学基于称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的脑扫描技术取得了许多进展。这些扫描通常被认为提供了对神经活动在各种刺激下详细分布的映射。然而,严格来说,fMRI 仅显示大脑不同区域血液含氧量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是实际神经活动的代表。因此,人们一直对这些复杂的 fMRI 信号是否可以由局部兴奋性神经活动增加触发的问题存在一些挥之不去的疑问。然而,今年 5 月,我的实验室使用光遗传学和 fMRI 的组合(称为 ofMRI)来验证局部兴奋性神经元的放电足以触发 fMRI 扫描仪检测到的复杂信号。此外,ofMRI 可以以以前使用电极或药物无法实现的精确度和完整性来绘制工作神经回路的图谱。因此,光遗传学正在帮助验证和推进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大量科学文献。
光遗传学也被用来控制一种被认为与嗜睡症有关的神经元(下丘脑泌素细胞),这是光遗传学在自由移动的哺乳动物中的首次应用。我们发现,这些神经元中特定类型的电活动会引发复杂的觉醒转变。光遗传学还被用来帮助确定制造多巴胺的神经元如何产生奖励和愉悦感。在这项与 Hsing-chen Tsai、Feng Zhang、Antonello Bonci、Garrett Stuber 和 Luis de Lecea 的合作中,我们在自由行为期间以不同的时间模式在小鼠中光遗传驱动了明确的多巴胺神经元,并发现了足以驱动强化行为的参数(例如,在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或奖励的情况下,健康的动物只是选择花更多时间在他们接受过特定类型的多巴胺神经元光遗传爆发活动的地方)。这项工作与抑郁症(正如我的抑郁症患者再也无法享受见到孙辈的乐趣,否则那是人类已知最有益的体验之一)和药物滥用以及健康奖励过程中涉及的享乐(与快乐相关的)病理学有关。
光遗传学方法也提高了我们对帕金森病的理解,帕金森病涉及大脑某些运动控制回路中信息处理的紊乱。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帕金森病患者通过一种名为脑深部刺激的疗法得到了缓解,该疗法使用一种类似心脏起搏器的植入设备,将精确计时的振荡电刺激应用于大脑深处的某些区域,例如丘脑底核。然而,这项技术在治疗帕金森病(以及其他多种疾病)方面的潜力受到了一定限制,因为电极会无选择地刺激附近的脑细胞,而且医学界对应该应用哪些刺激的理解还远远不够。然而,最近,我们使用光遗传学来研究帕金森病的动物模型,并对患病回路的性质和治疗干预的机制有了基本的了解。例如,我们发现脑深部刺激在靶向细胞之间的连接(影响大脑区域之间的活动流动)时可能最有效,而不是靶向细胞本身。而且,我们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Anatol Kreitzer 合作,他在大脑运动回路中功能性地绘制了两条通路:一条减缓运动,另一条加速运动,可以抵消帕金森病状态。
我们也了解了如何刺激一种细胞,即新皮质小白蛋白神经元,来调节大脑活动中每秒 40 次循环的节律,称为伽马振荡。科学界早就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小白蛋白细胞发生了改变,并且伽马振荡在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中都是异常的,但是这些关联(如果有的话)的因果意义尚不清楚。通过使用光遗传学,我的小组中的 Vikaas Sohal 和张锋(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李慧和 Chris Moore 以及我们的其他合作者)表明,小白蛋白细胞与其他细胞类型合作,有助于调节伽马波。反过来,这些波可以增强信息在皮层回路中的流动。在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我看到的信息处理问题显然很明显,其中平凡的随机事件被错误地视为更大主题或模式的一部分(信息问题可能导致妄想和妄想症)。这些患者可能遭受内部“通知”机制的某种故障,该机制会在自发产生的想法时通知我们(信息问题可能导致“听到声音”这种可怕现象)。相反,在我的自闭症谱系疾病患者中,我看到的信息处理过于受限,而不是信息中不恰当的广泛联系:他们只关注物体、人、谈话等的一部分,从而错过了大局。这些信息处理的失败可能会导致沟通和社交行为的失败,而对大脑节律的更好理解为这些复杂疾病提供了见解。
作为一名医生,我发现这项工作令人兴奋,因为我们正在将工程原理和定量技术应用于看似“模糊”但具有破坏性和棘手的精神疾病。因此,光遗传学正在帮助精神病学朝着网络工程方法发展,在这种方法中,大脑的复杂功能(及其产生的行为)被解释为神经系统的特性,这些特性是从组成细胞和回路的电化学动力学中产生的。因此,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兴奋性组织在健康和疾病中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解。我们已经从细菌视紫红质走了很长一段路,确实如此。
意想不到的收获
科学家们花费大量时间思考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实验室和他们自己的领域,还有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更一般性问题。在大型且多样化的科学聚会(例如,参加人数超过 30,000 人的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上,我偶尔会听到一些同事因该领域的多样性而感到不知所措,他们会采取辩护者的立场,并建议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集中在一个大型且紧急的项目上可能更有效,例如,消除阿尔茨海默病。实际上,科学中的一个常见话题和政策制定考虑的是,多样化的探索还是大规模的重点努力应该占主导地位的程度。即使对于小型重点努力,资助机构和科学组织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设定科学议程并指导研究人员?毫无疑问,定向方法和探索性方法都有价值,作为一名执业精神科医生,我充分理解定向努力的紧迫性。正如它们对我所做的那样,临床需求可以并且应该推动和激发基础科学和工程。
但是,应该如何准确地实现这种启发呢?光遗传学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即使像克里克那样设想了靶向神经元光学控制的概念,也没有预测到需要对微生物膜进行数十年的纯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预测古菌或藻类生物学对我们理解帕金森病及其治疗的影响。在人类走向理解自然世界的令人振奋的历史中,现在仍然为时过早。
研究越定向和有针对性,我们就越有可能减缓我们的进步,并且越能确定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想法可以产生的遥远而未知的领域将完全与我们共同的科学之旅隔绝。纯粹的定向资金将对最远离人类健康(例如古菌生物学)的领域产生最不利的影响,但甚至会阻碍明显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相关的领域,例如神经科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可以将 30,000 名科学家引导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专注于该目标的行为本身也可能确保无法实现该目标。
这些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应被低估。维护一个健康、不受约束的研究社区对我们的社会和全球健康的好处将以多种方式体现出来,从对精神疾病的洞察到对环境的保护。考虑一下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当被歪曲时,它可能会非常容易受到批评,就像光遗传学的案例一样,它可能会被不讨好地描述为花钱研究池塘浮渣中的基因。再次考虑一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就像在严酷、荒凉且毫无用处的撒哈拉盐湖中,一些最有用的视蛋白就起源于此。再次考虑一下脑部疾病的耻辱感,它与我们缺乏理解紧密相关。
在经典的微生物视蛋白研究中,我们为现代世界找到了意义,不仅对科学,而且对医学和精神病学,这为环境保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纯粹的理解探索做出了有力而明确的声明。而光遗传学的旅程表明,在我们已经走过或经过的地面下,可能存在着被现代社会忽视的必要工具,这些工具将使我们能够绘制出前进的道路。有时,这些被忽视或过时的工具正是最需要的,例如旧的、稀有的、小的和弱的工具。
多年前(在一段不受约束的阅读期间),我在《生物化学年鉴》中偶然发现了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家尤金·肯尼迪对他的职业生涯的思考,以及过去与未来、老年与新生、人类身体的死亡与艺术和科学的不朽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尼迪总结说:“几乎每一位科学家都会面临默默无闻的命运,因为一代人的工作几乎无痕地融入下一代人的工作,这是为其永无止境的进步,即人类理性的伟大长征所付出的一点代价。感觉自己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做出了贡献,无论规模多么小,都是一天辛勤劳动的足够回报。” 我只想在此宏伟的感言中补充一点,上面讲述的光遗传学的故事传达了一个有力而清晰的信息。在我们推动科学事业前进的过程中,我们绝不应忘记我们不知道这次漫长的征程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或者我们需要什么才能到达那里。
相关链接:
光遗传学资源中心
www.stanford.edu/group/dlab/optogenetics/index.html
微创脑刺激
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66/n7310_supp/box/466S15a_BX2.html
光遗传学新闻
www.forbes.com/forbes/2010/0719/opinions-lasers-algae-bioengineering-ideas-opinions.html www.stanford.edu/group/dlab/news.html www.hfsp.org/PDF_Files/Press%20release%20-%20Nakasone%20Award%202010%20to%20Karl%20Deisseroth_final.pdf
关于微生物视蛋白光遗传学的讲座
www.stanford.edu/group/dlab/karlsfntalk.html www.youtube.com/watch?v=C8bPbHuOZXg Karl Deisseroth 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和精神病学系的成员。他因开发微生物视蛋白和光遗传学而获得 2010 年国际中曾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