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研究人员像 Suzanne Simard 一样对流行文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位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态学家是理查德·鲍尔斯 2019 年普利策奖获奖小说《树木王国》中颇具争议的树木科学家帕特里夏·韦斯特福德的原型。Simard 的工作也启发了詹姆斯·卡梅隆在他 2009 年票房大片《阿凡达》中对神一般的“灵魂之树”的构想。她的研究还在德国林务员彼得·沃莱本 2016 年的非虚构畅销书《树木的隐秘生活》中得到了突出展示。
Simard 的发现俘获了公众的想象力,即树木是社会性生物,它们交换养分、互相帮助,并就虫害和其他环境威胁进行交流。
之前的生态学家专注于地上发生的事情,但 Simard 使用碳的放射性同位素来追踪树木如何通过一个错综复杂的 菌根真菌 网络相互分享资源和信息,这些真菌在树根上定殖。在最近的工作中,她发现有证据表明,树木能够识别自己的亲属,并将它们的大部分 bounty 给予它们,尤其是在树苗最脆弱的时候。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将帮助确保未来能够继续讲述关于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思想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
Simard 的第一本书,《寻找母亲树:发现森林的智慧》本周由克诺夫出版社出版。她在书中论证说,森林不是孤立生物的集合,而是不断演变的关系网络。她说,多年来,人类通过破坏性做法(如皆伐和灭火)一直在破坏这些网络。现在,它们正在导致气候变化加速,速度超过了树木的适应能力,导致物种死亡和害虫(如小蠹虫)的侵扰急剧增加,这些害虫已经摧毁了整个北美西部的森林。
Simard 说,人们可以采取许多行动来帮助森林(世界上最大的陆地碳汇)恢复,并在此过程中减缓全球变暖。在她最非常规的想法中,古老的巨树(她称之为“母亲树”)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需要热心保护它们。
[以下是访谈的编辑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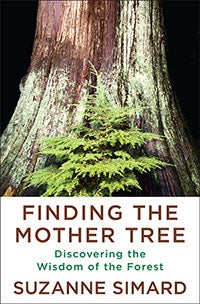
图片来源:克诺夫出版社
人们可能会惊讶于您在伐木家庭中长大——不完全是一群拥抱树木的人。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农村的童年经历如何为您作为科学家的生活做好准备?
像我小时候那样在森林里度过时光,您会知道一切都是交织和重叠的,事物彼此紧挨着生长。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系紧密的地方,即使我小时候无法清楚地表达出来。
在今天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伐木工人牺牲了桦树和阔叶树,他们认为这些树木与他们收获的冷杉争夺阳光和养分。作为一名年轻的政府树木科学家,您发现桦树实际上正在给冷杉幼苗提供养分,使其存活下来。
是的,没错。我被派去查明为什么人工林中的一些冷杉不如天然林中健康的幼年冷杉树长势良好。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是,在天然林中,桦树对花旗松幼苗的遮荫越多,桦树通过地下菌根网络为它们提供的光合糖形式的碳就越多。
桦树还富含氮,氮反过来支持细菌,这些细菌完成所有养分循环的工作,并在土壤中产生抗生素和其他化学物质,以对抗病原体并帮助产生平衡的生态系统。
但是,土壤细菌不是为自己产生抗生素,而不是为树木产生抗生素吗?我们怎么知道它们对树木有帮助呢?
桦树向土壤供应碳和氮,这些物质由根和菌根分泌出来,这为土壤中的细菌生长提供能量。在桦树根的根际生长的一种细菌是荧光假单胞菌。我进行了实验室研究,表明这种细菌与蜜环菌(一种攻击冷杉的病原真菌,对桦树的攻击程度较轻)一起培养时,会抑制真菌的生长。
您还发现桦树在夏季通过菌根网络向冷杉树提供糖分,而冷杉在春季和秋季(桦树没有叶子时)通过向桦树输送食物来回报。
这不是很酷吗?一些科学家对此感到困惑:一棵树为什么要向另一种物种输送光合糖?对我来说,这太明显了。它们都在互相帮助,以创建一个对每个人都有益的健康社区。
您是说森林社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自己的社会更平等、更有效率吗?这里有什么教训吗?
是的,它们促进多样性。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带来稳定性——它带来复原力,而且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物种协同合作。这是一个协同系统。一种植物具有很高的光合能力,它可以为所有这些固氮土壤细菌提供燃料。然后还有另一种深根植物,它向下扎根并提取水分,然后与固氮植物分享,因为固氮植物需要大量水分才能开展活动。因此,突然之间,整个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大幅提高。
因为物种之间互相帮助吗?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我们一直未能理解的概念。
因此,合作与竞争同等重要,甚至比竞争更重要。我们需要修正我们对自然运作方式的看法吗?
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做。[查尔斯] 达尔文也理解合作的重要性。他知道植物共同生活在群落中,并且对此进行了描述。只是它从未像他基于竞争的自然选择理论那样受到关注。
如今,我们审视人类基因组等事物,意识到我们 DNA 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病毒或细菌。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自身就是共同进化的物种联盟。以这种方式思考正变得越来越主流。同样,森林也是多物种组织。土著文化了解这些联系和互动以及它们的复杂程度。人类并非一直持有这种还原论方法。这是西方科学发展的结果,它将我们引向了这一步。
您的意思是西方科学过于关注个体生物,而对更大群落的功能关注不足吗?
是的,但我也认为科学一直在进步。我们从非常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观察单个生物,然后我们观察单个物种,然后我们开始观察物种群落,然后是生态系统,然后是更高层次的组织。因此,西方科学已经从简单走向复杂。随着我们自身变得更加成熟,它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它变得更加整体化。
您使用“智能”一词来描述树木是有争议的。但您似乎正在提出一个更激进的论断——整个生态系统中存在“智能”。
您使用了“有争议”这个词。这源于我使用人类术语来描述一个高度进化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实际上具有与我们大脑非常相似的结构。它们不是大脑,但它们具有智能的所有特征:行为、反应、感知、学习、记忆存档。并且通过这些网络发送的是[化学物质],例如谷氨酸,谷氨酸是一种氨基酸,也在我们的大脑中充当神经递质。我称该系统为“智能”,因为这是我在英语中能找到的最能类比我所看到情况的词语。
有些人质疑您使用“记忆”等词语。我们有什么证据表明树木实际上“记住”了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情?
过去事件的记忆存储在树木年轮和种子的 DNA 中。树木年轮的宽度和密度,以及某些同位素的自然丰度,都保存着往年生长条件的记忆,例如是湿润年还是干旱年,或者附近是否有树木,或者它们是否被吹倒,从而为树木生长得更快创造了更多空间。在种子中,DNA 通过突变以及表观遗传学进化,反映了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的遗传适应。
您在书中写道:“通过倾听而不是强加我的意愿和索取答案,我学到了更多。” 您能谈谈这一点吗?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们受到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它可能非常僵化。有非常严格的实验设计。我不能只是去观察事物——他们不会发表我的作品。我必须使用这些实验设计——我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我的观察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非常重要。它们始终来自我的成长经历、我对森林的看法以及我的观察。
您最新的研究项目被称为母亲树项目。什么是“母亲树”?
母亲树是森林中最大、最古老的树木。它们是将森林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它们拥有来自先前气候的基因;它们是许多生物、许多生物多样性的家园。通过其巨大的光合能力,它们为整个土壤生命网络提供食物。它们将碳保留在土壤和地上,并保持水分流动。这些古老的树木有助于森林从扰动中恢复。我们不能失去它们。
母亲树项目试图在真实的森林中应用这些概念,以便我们可以开始管理森林以实现复原力、生物多样性和健康,认识到我们实际上已通过气候变化和过度采伐将它们推向崩溃的边缘。我们目前正在 9 个森林中工作,这些森林的范围从美国-加拿大边境延伸到圣詹姆斯堡,大约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中途。
《树木王国》中受您启发的人物帕特里夏·韦斯特福德有时会感到绝望。您有时也会感到沮丧吗?
当然我会。但我没有时间感到沮丧。当我开始研究这些森林系统时,我意识到它们的组织方式使它们能够非常迅速地恢复。您可以将它们推到崩溃的边缘,但它们具有巨大的缓冲能力。我的意思是,大自然是辉煌的,对吧?
但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将需要稍微帮助大自然。我们将不得不确保母亲树在那里帮助下一代向前发展。我们将不得不将一些预先适应温暖气候的基因型移入更北部或更高海拔的森林,这些森林正在迅速变暖。气候变化的velocity远快于树木自身迁移或适应的velocity。
将种子从一个综合生态系统转移到另一个生态系统是否存在风险?
尽管再生本地适应的种子是最好的,但我们改变气候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森林将需要帮助才能生存和繁殖。我们必须协助已经预先适应温暖气候的种子的迁移。我们需要成为积极的变革推动者——生产性推动者而不是剥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