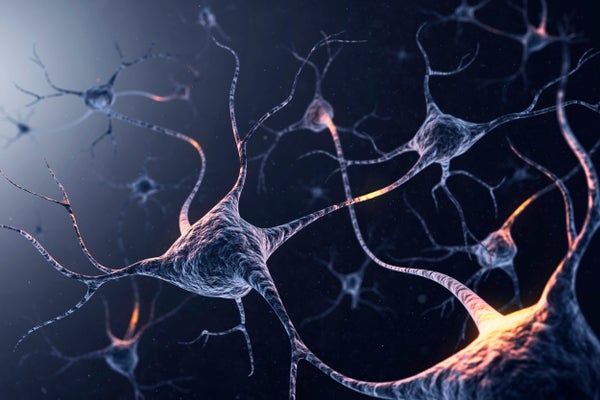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周一报告称,他们通过注射RNA将记忆从一只动物转移到另一只动物身上,这一惊人的结果挑战了关于记忆在大脑中存储位置和方式的普遍观点。
大卫·格兰兹曼实验室的这一发现暗示了未来可能出现基于RNA的新疗法,以恢复失忆症,如果正确的话,可能会撼动记忆和学习领域。
“这非常令人震惊,”纽约州布鲁克林区纽约州立大学下城医疗中心的神经学家和记忆研究员托德·萨克托博士说。“重要的是,我们首次研究出记忆存储的基本字母表。” 他没有参与这项研究,该研究发表在eNeuro上,这是神经科学学会的在线期刊。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 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许多科学家预计会更加谨慎地看待这项研究。这项工作是在蜗牛身上进行的,蜗牛已被证明是神经科学的强大模型生物,但其简单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运作方式截然不同。这些实验需要重复,包括在具有更复杂大脑的动物身上进行。而且,这些结果与大量证据相悖,这些证据支持根深蒂固的观点,即记忆是通过神经元之间连接或突触强度的变化来存储的。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助理教授托马斯·瑞安说:“如果他是对的,这将是绝对惊天动地的。”他的实验室正在寻找记忆的物理痕迹,即印迹。“但我不认为他是对的。”
格兰兹曼知道他对突触的非正式降级不会在该领域引起共鸣。“我预计会感到震惊和怀疑,”他说。“我不期望人们会在下一次神经科学学会会议上为我举行游行。”
甚至他自己的同事也表示怀疑。“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我实验室的人做这个实验,”他说。“他们认为这太疯狂了。”
格兰兹曼的实验——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包括对海蜗牛加州海兔进行轻微的电击。受到电击的蜗牛学会收回其脆弱的虹吸管和鳃近一分钟,作为随后受到轻微触摸时的防御;未受到电击的蜗牛只会短暂收回。
研究人员从受到电击的蜗牛的神经系统中提取了RNA,并将该物质注射到未受到电击的蜗牛中。RNA的主要作用是在细胞内充当信使,携带来自其近亲DNA的蛋白质制造指令。但是,当注射这种RNA时,这些未受刺激的蜗牛在受到轻柔触摸后,将其虹吸管收回了很长时间。接受了未受到电击的蜗牛的RNA注射的对照蜗牛,其虹吸管收回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格兰兹曼说:“就好像我们转移了记忆一样。”
格兰兹曼的研究小组更进一步,表明如果将培养皿中的海兔感觉神经元暴露于来自受到电击的蜗牛的RNA,它们会变得更兴奋,就像受到电击后一样。暴露于来自从未受到电击的蜗牛的RNA不会导致细胞变得更兴奋。
格兰兹曼说,结果表明记忆可能存储在神经元的细胞核内,RNA在那里合成,并且可以作用于DNA以开启和关闭基因。他说,他认为记忆存储涉及这些表观遗传变化——基因活动的改变,而不是构成这些基因的DNA序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RNA介导的。
这种观点挑战了广泛持有的观点,即记忆是通过增强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来存储的。相反,格兰兹曼认为,记忆形成过程中发生的突触变化源于RNA携带的信息。
麻省理工学院皮考尔学习与记忆研究所所长、神经科学家李慧表示:“这个想法很激进,绝对挑战了这个领域。” 蔡最近与人合著了一篇关于记忆形成的主要综述,她称格兰兹曼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且有趣”,并表示许多研究支持表观遗传机制在记忆形成中发挥一定作用的观点,这可能是一个复杂且多方面的过程。但她说,她强烈反对格兰兹曼的观点,即突触连接在记忆存储中不起关键作用。
与格兰兹曼一样,圣三一学院的瑞安也与少数神经科学家(有些人称他们为叛逆者)站在一起,他们质疑记忆是通过突触强度存储的想法。2015年,瑞安是《科学》杂志一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该论文与麻省理工学院诺贝尔奖获得者利根川进合作,表明即使在突触加强被阻止后,记忆也可以被检索。瑞安说,他正在研究这样一种观点,即记忆是通过由新的突触连接结合在一起的神经元集合来存储的,而不是通过加强现有连接。
瑞安认识格兰兹曼并信任他的工作。他说他相信新论文中的数据。但他不认为蜗牛或细胞的行为证明RNA正在转移记忆。他说,他不明白RNA如何在几分钟到几小时的时间尺度内工作,如何引起几乎瞬间的记忆回忆,或者RNA如何连接大脑的许多部分,例如听觉和视觉系统,这些部分参与更复杂的记忆。
但格兰兹曼说,他确信RNA正在发挥超越突触的作用。2014年,他的实验室表明,由于一系列实验程序而在蜗牛中丢失的电击记忆可以被恢复——但是当记忆恢复时,与记忆一起丢失的突触模式以随机方式重新形成,这表明记忆并非存储在那里。格兰兹曼的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也表明,即使突触形成或加强没有改变,阻止表观遗传变化也会阻止长期记忆的形成。
他说:“突触可以来来去去,但记忆仍然可以在那里,”他说,他认为突触仅仅是“细胞核中持有的知识的反映”。
格兰兹曼研究记忆已有三十多年。他与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一起做了博士后工作——这位神经科学家因对海兔的研究而分享了2000年诺贝尔奖,探索了突触在记忆中的作用——他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相信突触变化是记忆存储的关键。
但他说,近年来来自其他实验室和他自己实验室的一系列发现使他开始质疑突触教条。他称自己为“康复中的突触学家”。
对格兰兹曼研究的怀疑可能部分是由于这项工作让人回想起科学界令人不安的一幕,涉及一位非常规心理学家詹姆斯·V·麦康奈尔,他曾在密歇根大学花费多年时间试图证明大脑外部的某种东西——他称之为“记忆RNA”的因素——可以转移记忆。在50年代和60年代,麦康奈尔训练了扁虫,然后将训练过的蠕虫的身体喂给未经训练的蠕虫。未经训练的蠕虫随后似乎表现出它们吞噬的训练有素的蠕虫的行为,这表明记忆以某种方式转移了。他还表明,训练过的蠕虫在被斩首后可以记住它们的训练,即使它们长出了新的头。
尽管这项工作被其他一些实验室复制,但麦康奈尔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嘲笑,并且经常被描述为一个警示故事,因为其他实验室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试图(通常是不成功地)复制这项工作。(麦康奈尔于1990年去世,五年前他曾是炸弹客西奥多·卡辛斯基的目标。)
最近,塔夫茨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迈克尔·莱文在更受控制的环境下复制了麦康奈尔的无头蠕虫实验,并认为麦康奈尔可能确实是正确的。
格兰兹曼说,麦康奈尔的一位学生艾尔·雅各布森在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期间,巧合地证明了通过RNA注射在扁虫之间转移记忆。这项工作发表在1966年的《自然》杂志上,但雅各布森从未获得终身教职,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他的发现表示怀疑。然而,该实验不久后在老鼠身上得到了重复。
格兰兹曼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心理学本科时了解了麦康奈尔的工作——以及他的讽刺期刊《蠕虫赛跑者文摘》——但从未认真对待这些结果。现在,虽然他仍然不相信麦康奈尔完全正确地认为能够转移记忆,但他确实认为麦康奈尔和雅各布森都发现了一些东西。
对于那些挑战现状的人来说,在记忆领域工作可能很艰难。例如,纽约州立大学的萨克托花了超过25年的时间——尽管受到同行科学家的怀疑、拒绝和彻底嘲笑——追逐一个单一分子PKMzeta,他认为该分子对于长期记忆的形成至关重要,并且可能与格兰兹曼发现的RNA机制有关。
该领域的风险很高,因为记忆对我们的自我意识至关重要,许多科学家认为,理解记忆的运作方式是现在应该弄清楚的事情。“这是20世纪生物学中最后一个伟大的问题,”萨克托说。“某些方面使得神经科学家难以弄清楚。”
部分原因可能是过度关注突触强度。瑞安指出,大约有12,000篇关于突触强度的论文发表,但没有对记忆如何存储提供充分的解释,他补充说,他赞赏格兰兹曼开辟了一条探索的新途径,尽管它很激进。
瑞安说:“现实情况是,我们对记忆知之甚少。“我对任何新的视野和途径都感到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