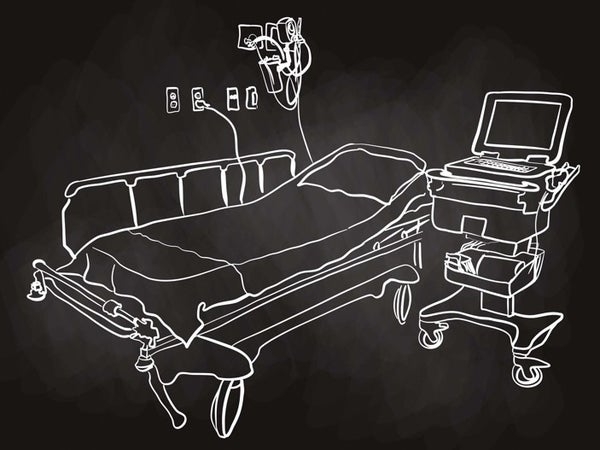2016年,加拿大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将自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之一。自从新规通过以来,居住在那里的患有“严重且不可补救的医疗状况”的人可以选择通过施用致命的药物混合物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许多医疗组织,包括世界医学协会,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更深层的伦理困境:一些寻求医生协助死亡的患者也表达了他们希望将自己的组织捐赠给科学研究,以帮助研究人员在未来几代人中治疗和治愈他们的疾病。
已经有几位患有晚期多发性硬化症 (MS) 的人自愿在接受自愿安乐死(在加拿大正式称为医疗辅助死亡)后捐赠脑组织样本用于医学研究。他们的组织在他们去世后一小时内被收集,对于收集脑组织样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短暂时间窗口,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和尸检之间的时间间隔过长,组织就会降解,”蒙特利尔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亚历山大·普拉特说。这使得几乎不可能确定与 MS 相关的脑损伤内部基因和蛋白质的活动。普拉特称之为“超新鲜”的脑组织样本在死亡后不久收集,研究人员可以访问这些信息。他说,这样做可能会揭示疾病的根本原因,并最终带来改进的治疗方法。
尽管潜在的科学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该实践的伦理道德却比较模糊,并且它们对患者、他们的亲人以及全球医学界都具有影响。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将帮助确保有关当今塑造我们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对 MS 等疾病的研究传统上因疾病动物模型的使用而变得更容易。最近,三维脑“类器官”已成为研究 MS 的一种很有前景的新工具。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通过研究从患有这种疾病的人身上采集的组织样本而获得的见解。
“说‘我们在大鼠模型中看到了这种生物学反应或作用机制,我们认为这些可能与人类相关’,这当然很好,”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和脊柱外科医生布 Brian Kwon 说。“但有机会在人类患者身上测试这些假设则是另一回事。”
但普拉特说,从患有 MS 等疾病的人身上收集脑组织样本具有挑战性。他说,大脑愈合不良,这使得研究人员无法从患有这种疾病的活人身上获取活组织检查样本。这意味着脑组织样本必须在死后采集。有传闻证据表明,一些 MS 患者渴望捐献他们的大脑用于研究。例如,当在2017 年为数字出版物《今日多发性硬化症新闻》撰写的文章中提出这个主题时,几位 MS 患者在该文章下方留言,表达了捐献自己大脑的意愿。“我没想到 MS 患者被允许捐献器官,”一位评论员写道。“我想捐献我的 MS 大脑来帮助 MS 研究。”
但普拉特说,如果在宣布死亡和样本采集之间存在 significant 延迟,组织就会失去其医疗价值。他说,死亡和尸检之间仅等待五到六个小时,只有稳定的蛋白质才能在样本中检测到。“不稳定的蛋白质会被降解,RNA 将毫无用处。就我们可以在病理学层面研究的内容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在加拿大允许辅助死亡的新法律生效后,普拉特和他的同事联系了一些选择接受医学安乐死的 MS 患者,询问他们是否也会考虑捐赠脑组织样本用于研究。加拿大法律的撰写方式意味着,如果患有严重但非绝症(如 MS)的人的健康状况非常差,以至于死亡被认为是“合理可预见的”,他们可能有资格接受医学安乐死。此外,在加拿大接受辅助死亡的人中,略低于一半的人在医院环境中这样做,这意味着尸检小组可以待命在附近的尸检室中,以便在宣布死亡后不久收集组织。
普拉特说,到目前为止,大约有六个人接受了辅助死亡,并同意捐赠他们的组织用于普拉特领导的研究。亲人可以在宣布死亡后与患者待在一起长达一个小时,进行最后的告别,然后将遗体转移到尸检室。取出此人的大脑并对与 MS 相关的病变进行取样。其中一些样本留在普拉特的机构;另一些样本立即运往远在美国和法国的合作者。普拉特说,研究小组正在使用一种称为单细胞 RNA 测序的技术来计算样本中不同形式 RNA 的数量。他们还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来表征不同脑损伤内的组织,并使用流式细胞术来识别特定的细胞类型。
普拉特表示,MS 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因此确定个体脑损伤的确切细胞和分子特征具有真正的价值。“在 MS 中,大脑有数百或数千个损伤,每个损伤都不同,”他说。他和他的同事正在收集的数据将用于构建一个数据库,以探索这种变异的极限。它最终可能会为针对个体患者量身定制的 MS 带来更好的治疗选择。
阿姆斯特丹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 Inge Huitinga 说:“尸检延迟越短,脑组织质量越好。” “短暂的尸检延迟允许对组织进行最先进的分析。”
Huitinga 是荷兰脑库的主任,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该脑库接受了来自患有各种神经和精神疾病的捐赠者以及死时大脑健康的人的尸检样本。
荷兰脑库中少量大脑来自接受安乐死的捐赠者,安乐死自 2002 年以来在荷兰是合法的。然而,Huitinga 说,根据她的经验,这些大脑与以其他方式死亡的人捐赠的大脑在质量上几乎没有差异。原因之一是,在荷兰,超过 80% 符合安乐死条件的人选择在家中接受该手术。这意味着,即使可以提前确定死亡时间和日期,但在将遗体运送到医院期间以及尸检开始之前,仍然存在延迟。她说:“最终,由于荷兰的医疗辅助死亡,平均尸检延迟时间并没有缩短。”
伦理考量
因此,普拉特的研究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加拿大有一半接受自愿安乐死的人在医院进行安乐死,因此该国可能是唯一一个通常可以在宣布死亡后一小时内收集脑组织样本的地方。特雷弗·斯塔默斯是英国伦敦圣玛丽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他研究安乐死和辅助自杀的伦理道德,他不知道有人以普拉特及其同事的方式收集样本进行研究。但斯塔默斯说,普拉特的工作提出了一些熟悉的伦理问题,因为在少数几个国家,已经可以捐赠器官(主要是肝脏和肾脏)用于自愿安乐死后的移植。
比利时和荷兰大约十年前就开始进行此类手术,现在加拿大也在进行此类手术。比利时鲁汶大学医院的胸外科医生 Dirk van Raemdonck 表示,器官捐赠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用于诱导死亡的巴比妥类药物、吗啡和麻痹剂的混合物似乎对为捐赠而收获的器官没有毒性作用。
同样,需要在死后尽快开始尸检,以便可以在器官退化之前收集器官——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与脑组织收集相关的紧迫性没有那么高,并且通常认为延迟几个小时是可以接受的,van Raemdonck 说。但斯塔默斯说,即使这种在安乐死后略微降低的医疗紧迫感也可能会扰乱亲属的哀悼过程。他认为,如果遗体在他们有时间自己确认之前就被移走,甚至可能导致他们后来不确定他们的亲人是否真的死了。
普拉特从 MS 患者身上收集脑组织样本的经验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家属被告知,他们可以在宣布死亡后与亲人单独相处约 60 分钟,以便他们实现情感上的解脱,但他表示,许多人选择放弃这项权利,以便尸检可以更快地开始。
然而,斯塔默斯想知道家属是否真的对这个过程感到安心。他怀疑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如果他们花太多时间与遗体在一起,并危及组织或器官的医疗价值,他们会辜负医生。
世界医学协会医学伦理委员会主席兼丹麦医学协会主席 Andreas Rudkjøbing 提出了另一个担忧。始终向那些申请安乐死的人强调,他们可以随时撤回他们的请求。但是,如果安乐死候选人随后也同意在他们死后捐赠组织用于医学研究,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拒绝进行安乐死的选择,同样是因为他们担心让医生失望。“如果患者承诺参与研究,他或她将更难改变主意,”他说。
现在说这些担忧是否会在现实世界中发生可能还为时过早。
但是,对从接受辅助死亡的人那里获得的样本进行 MS 研究会引发其他伦理复杂性。原则上,普拉特及其合作者进行的研究可能会为 MS 带来新的疗法,使全世界的人们受益,包括那些自愿安乐死仍然是非法的甚至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国家的患者。
“我认为这令人担忧,”Rudkjøbing 说。“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安乐死,我们同样反对利用安乐死的做法来促进临床研究。”
牛津大学医学伦理学家多米尼克·威尔金森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知识本身不具有伦理价值。一些研究人员可能会对利用从选择自愿安乐死的人那里获得的细胞系进行研究感到不舒服。但威尔金森说,研究人员忽视其他人通过研究此类组织获得的知识,在伦理上更没有意义。
也许需要牢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公众如何看待普拉特等人的研究。如果人们愿意在死后捐献他们的组织和器官(无论是自然死亡、意外死亡还是医疗辅助死亡),将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只有当人们感到他们可以信任捐赠过程时,他们才可能准备好成为捐赠者。斯塔默斯担心,如果围绕捐赠的讨论与围绕有争议的自愿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混淆,一些原本会考虑捐赠组织用于研究的人可能会决定不捐赠。
“我非常支持器官和组织捐赠,”斯塔默斯说。“因此,我担心任何可能危及它并损害对其有效运作至关重要的信任的事情。”
本文经许可转载,并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