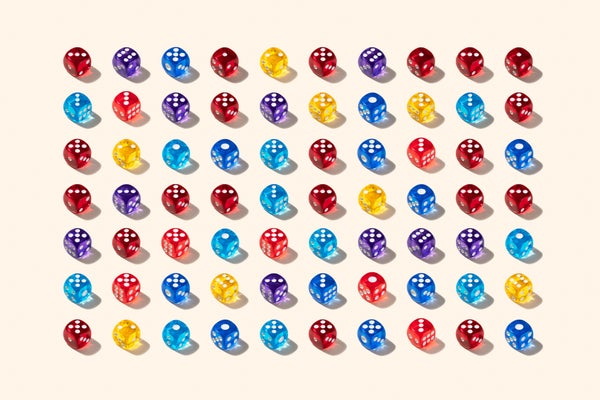COVID-19 的冲击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不确定性。如果病毒对我们肉眼可见,我们本可以避开它,并像往常一样进行其他活动。不仅我们看不到病毒本身,我们也看不到某些可能感染我们的人身上的症状。因此,我们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远远超出了我们显著暴露的特定地点和时间的比例。我们避免与对我们没有风险的未感染者互动,我们也不参加本可以使我们的经济保持运转甚至继续繁荣的活动。当有毒昆虫在附近时,我们会待在原地,仅仅因为我们看不到它。
在阿尔贝·加缪的书《鼠疫》中,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生动地阐释了我们存在的现实。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死去,但我们无法为此做好准备,因为我们无法预测它何时会发生。存在的不确定性不仅延伸到我们的私人生活,也延伸到社会领域。 越南战争是由对北部湾事件的模糊解释引发的,并塑造了一代人的生活。
人们可能会天真地认为,我们生活中的基本不确定性仅仅反映了信息的缺乏;通过追踪缺失的信息,我们就能够清除未知的迷雾。然而,量子力学,它是我们物质现实的基础,暗示着我们能够期望达到的清晰度是有限的。 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指出,对于某些可观测对象,总是存在残留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试图完善我们对电子位置的了解,我们的测量过程将增加其动量的不确定性。位置和动量不确定性的乘积有一个由普朗克常数设定的基本最小值。
关于支持科学新闻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订阅以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工作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当今塑造我们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这意味着即使我们通过一个完美的实验检索到所有可用信息,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地预测电子的未来。传统上,我们的生活是由大型物体塑造的,例如我们驾驶的汽车,对于这些物体来说,海森堡的不确定性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出现,量子世界最终可能会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影响医疗决策。现实的基石是概率性的。我们只能为不同的结果分配可能性。
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26年写给马克斯·玻恩的信相反,我们现在知道大自然确实掷骰子。我们感染 COVID-19 后总是存在一定的死亡概率。那些在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参加泳池派对的人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活下来,但有些人会死去。
当然,医疗方面的既往病史可能会强烈影响 COVID-19 死亡等罕见结果。现实生活中的事件通常源于多种原因的汇合,因此很难解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明确地识别出某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受控科学实验背后的原因,它提供了在寻求更好理解的过程中一次隔离一种影响的机会。
当数据稀缺时,科学界的看法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最近对病毒突变的RNA测序显示,COVID-19在美国的感染路径与之前认为的非常不同。
但是,即使收集了大量数据,我们理解其真正含义的能力也会限制我们预测的可靠性。玛雅文化在许多世纪中收集了大量的天文数据,并将他们的天空图像与人类历史相关联,以达到预测战争结果的政治目的。我们现在知道,人类行为中隐含的不确定性,就像在越南战争中一样,无法通过监测月球、水星、金星、火星、木星或土星的天空位置来消除。相反,当前科学的目的是以可重复的方式将原因与结果联系起来,而没有一厢情愿或偏见。天文学教育我们,行星和恒星的运动与人类的行为无关,而遗传学则启发我们,人类的能力与肤色无关。
尽管如此,我们的科学理解中仍然存在巨大的空白。因此,许多人在面对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是否参加泳池派对)的不确定性时,依赖于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这是基于过去的经验,那似乎很自然,但当类似的疫情在1918年肆虐时,年轻的派对参与者还不存在。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贯穿我们生活的基本不确定性?负责任的建议很简单:我们应该考虑所有科学证据,并对未知事物采取有分寸的风险。每次过马路时,我们都会进行这样的计算。只有傻瓜才会因为存在的风险而永远不过马路。回报通常以风险为前提。如果你想学会游泳,你必须跳入水中;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你冒着溺水的风险。目前,在科学家为 COVID-19 研制出可靠的疫苗之前,你最好避开任何公共游泳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