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什么? 像大多数伟大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很容易提出,但很难回答。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尝试,哲学家们则进行了数千年。 今天,我们的知识如此先进,以至于我们可以精确地操纵生命的基石——DNA、RNA 和蛋白质——来构建生物机器和设计新的基因组。 然而,尽管我们知道这么多,但目前对于生命的基本定义仍未达成普遍共识。
生命的定义仍然难以捉摸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只知道一种类型的生命——地球上存在的生命——并且用一个样本量来做科学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 这就是所谓的 N = 1 问题(其中“N”表示科学家可以研究的合格候选者的数量)。 无论研究人员多么聪明地从他们确定的唯一实例中推断出生命的一般原则,他们都无法确认他们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除非 N 增加。 寻找生命的另一个实例——无论它是在地球上、太阳系的其他地方还是更远的地方被发现——是扩大 N 的一种方法。 对外星生命(以我们未知的方式存在)的寻找才刚刚开始,但它已经耗费了数十亿美元和无数小时的劳动,即使不能保证最终会有所发现。
然而,还有另一种解决 N = 1 问题的潜在方法:一些科学家没有去寻找生命的第二次起源,而是试图创造一个。 人造生命领域——简称 ALife——是有系统地阐明生命基本原则的尝试,通过研究表现出类似生命行为的无生命自然系统,或通过构建人造系统来与自然界的创造物进行比较。 许多实践者,即所谓的 ALifers,认为从头开始创造生命是真正理解生命是什么的最可靠方法——这种方法也许最好概括为“先构建,后解释”。
支持科学新闻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 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剧透警告: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新兴领域中,还没有人令人信服地创造出人造生命——但这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 这种明显糟糕的记录使 ALife 成为各种批评的众矢之的,从“扮演上帝”的指责到该领域可疑的科学价值的宣告。
东京大学的复杂性科学家池上高志 (Takashi Ikegami) 厌倦了这些抱怨。 他说,他的领域就像任何其他追求知识本身的基础科学一样,所以询问 ALife 的“意义”可能完全没有抓住重点。
“生命系统的存在与任何事物的功用无关,” 池上说。 “有些人问我,‘人造生命的优点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你祖母的优点是什么? 你狗的优点是什么?’”
无尽的进化
尽管许多 ALifers 不愿强调他们研究的应用,但创造人造生命的探索也可能带来实际的回报。 人工智能可以被认为是 ALife 更迷人的表亲,因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沉迷于一个名为开放式进化的概念。 这是一种系统创造本质上无限复杂性的能力,成为一种“新颖性生成器”。 已知唯一表现出这种特性的系统是地球生物圈——一个持续不断、数十亿年的生物多样性进化爆发,最终可以追溯到简单的单细胞祖先生物。 如果——或者当——ALife 领域设法在某些虚拟模型中复制生命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力”时,那么相同的原理可能会产生真正具有创造力的机器。
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你可以构建这些庞大的深度学习系统,但在某些时候,这些系统无法再学习,” 南丹麦大学的 ALife 研究员兼物理学家斯蒂恩·拉斯穆森 (Steen Rasmussen) 说。 “一个系统要继续学习需要什么? 没人知道。”
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相比,ALife 的进展更难被认可。 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是,ALife 是一个核心概念——生命本身——令人烦恼地未定义的领域。 ALifers 之间缺乏共识也无济于事——没有一套共同的原则来指导他们的集体工作,更不用说评估它的标准了。 结果是各种各样但漫无目的的项目,每个项目都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随意前进。 无论好坏,ALife 都反映了它所研究的主题。 它混乱的进展与塑造地球生物圈的漫长进化斗争惊人地相似。
组装 ALife
ALife 的非官方启动始于 1987 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举行的首届生命系统合成与模拟跨学科研讨会,该领域在那里获得了名称的合法性。 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托弗·兰顿 (Christopher Langton) 创造的“人造生命”一词为科学怪才和流浪者对类生命行为的零散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签。 拉斯穆森是 36 年前参加研讨会的与会者之一。 他回忆起感觉自己“回到了家”。
一些 ALife 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 1948 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 (John von Neumann) 和斯坦尼斯瓦夫·乌拉姆 (Stanislaw Ulam) 着手阐述机器在理论上如何能够自我复制——ALifers 后来将此特征作为生命的标志。 数学家们用笔在纸上构建了细胞自动机的概念,这是一种由在二维网格上跳跃的阴影或无阴影单元组成的动态实体。 在冯·诺伊曼和乌拉姆的公式中,每个单独的单元根据与其邻居的简单关系规则闪烁或关闭。 根据组成单元的初始位置,它们的簇可以展示出令人惊讶的复杂行为,例如无限期的自我复制。 数学家们对细胞自动机的研究帮助他们意识到,复制活细胞必须能够以某种方式内化和记录有关其环境的信息——这一洞察力预示着当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DNA 作为地球生命信息存储分子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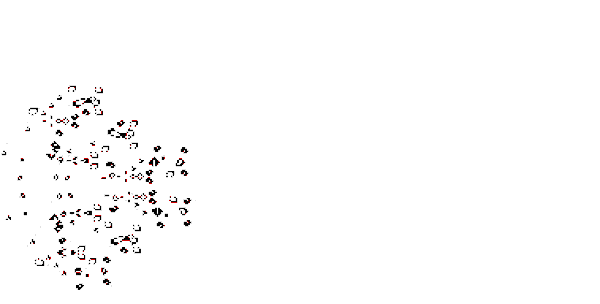
此动画显示了“繁殖者”(红色突出显示)的演变过程。 繁殖者是康威生命游戏中细胞自动机的一个类别,它通过生成辅助模式(绿色)的多个副本来生长,每个副本随后又生成三级模式(蓝色)的副本。 这种简单的系统可以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复杂性,但不符合“生命”的各种其他定义标准。 鸣谢: George 对讨论的衍生作品,以及 Hyperdeath/Wikimedia Commons 的 Conways_game_of_life_breeder.png (CC BY-SA 3.0)
当数学家约翰·康威 (John Conway) 在二十多年后设计了生命游戏时,这些细胞自动机与人造生命追求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首次在 1970 年 10 月版的《大众科学》上普及,这是一个扩展冯·诺伊曼和乌拉姆规则的游戏概念。 很快,康威游戏的各种版本开始在早期的数字计算机上大规模运行,从而更容易探索出现的复杂模式和复杂行为。 生命游戏风靡一时,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玩家成为扶手椅实验家,在他们屏幕上闪烁的像素星座中寻找新的数字“生物”。
从卑微的开端开始,最终出现了 ALife 的三个不同分支。 所谓的“软”Alife,例如生命游戏,在计算机上模拟生命。 另一个称为“硬”ALife 的分支涉及自主机器人的创造。 第三个分支“湿”ALife 涉及使用已知的生物化学原理创造合成生物体。
在这些分支中,硬 ALife 在迈向第二次起源的竞赛中落后于其他分支。 迄今为止,没有机器人可以在没有人类或其他机器的外部帮助下自发组装自身。
基于软件的生物体,即软 ALife 的例子,已经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它们中的一些可以在托管它们的计算机上进化并争夺空间和时间资源。 其中一个例子是生态学家托马斯·雷 (Thomas Ray) 开发的虚拟宇宙 Tierra,其特点是实体从一代到一代地复制、变异和相互竞争。 但是,这种虚拟化的“适者生存”仍然未能满足开放式进化的标准:Tierra 及其同类产品中数字生物体的复杂性和新颖性最终会趋于平稳。
基于化学的湿 ALife 研究最接近真实生物学,并且通常获得最高的科学尊重。 例如,在 2010 年代的一系列实验中,遗传学家 J. 克雷格·文特尔 (J. Craig Venter) 及其团队成功地将合成基因组移植到中空的支原体细菌中,以创造出定制的自我复制细菌细胞。 2021 年,另一个科学家团队将成团的青蛙细胞塑造成“异种机器人”,它们可以在培养皿中游动。 这些移动的斑点还可以将分散的青蛙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新的异种机器人——这是自我复制的另一个证明。
学习经验
最近,混合方法已经出现,专注于“生命”难题的较小部分。 例如,去年 9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模拟简单的化学系统如何表现出学习能力,将湿 ALife 和软 ALife 结合起来。 学习是生命的标志,因为它使生物体能够在环境突变中生存下来。 从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更大范围来看,进化可以被认为是通过选择性适应不断变化的栖息地来学习。 这项工作由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斯图尔特·巴特利特 (Stuart Bartlett) 和法国程序员大卫·卢阿普尔 (David Louapre) 完成,展示了只有少数虚拟化学反应如何构成简单模拟化学混合物的长期和短期记忆,以寻求保护免受反复出现的“毒素”剂量的侵害。 在反复中毒后,化学系统可以“学习”以确定制造“解毒剂”的时间——既可以先发制人也可以事后使用——以在化学威胁中生存下来。
拉斯穆森说,这项研究是“非常好的工作”,他没有参与这项研究。 他说,这是因为它将认知某些基础可能出现在生命出现时的阈值向后推。“我们不知道 [它] 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如此复杂的行为,” 他补充道。
自由机器学习研究顾问尼古拉斯·古滕贝格 (Nicholas Guttenberg) 说,巴特利特和卢阿普尔可能已经证明了迄今为止最简单的化学学习形式,但他没有确定非学习系统最初是如何开始学习的,古滕贝格也没有参与这项研究。 他指出,“学习”能力是巴特利特和卢阿普尔必须预先编程到他们的模拟中的东西。 他说,这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学习是否会在没有首先人为设计的关系的情况下自发出现?”
这些问题并没有让巴特利特气馁,他认为他的虚拟化学混合物是最低限度活着的。 它们消耗自由能、呈指数增长、稳定内部过程并了解环境——所有这些都是巴特利特个人对“生命”的工作定义的标准。 它们甚至可以复制——但它们不会代代相传地偏离,因此它们无法实现任何类似生命的复杂性失控增长。
存在危机
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的生物化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 (Stuart Kauffman) 说,即使开放式进化是创造人造生命最后剩下的一个待勾选的方框,该社区的努力也可能注定要失败。 考夫曼被视为 ALife 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现在认为实现开放式进化是该领域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 ALife 研究从根本上与科学方法不相容。
考夫曼说,科学通过逻辑演绎来概括收集到的观察结果,从而形成一个总体理论。 但不可预测性是生命开放式进化的本质,因此科学的分析方法无法预先预测野生物种的进化轨迹,他说。
用进化生物学的术语来说,生命被认为是“外适应”的,这意味着它可以将预先存在的组件用于新的功能。 控制现代鱼类浮力的鱼鳔被认为是从古代祖先的肺进化而来的。 让史前鸟类保持温暖的羽毛逐渐被重新用于飞行和求偶炫耀。“任何东西都有无限多的可能用途,” 考夫曼说。 预测进化将如何将一个特征转向其下一个用途的问题不是掷骰子的问题; 而是预测何时会有人出现并掷骰子打破附近的窗户。

一位艺术家对曙光鸟的构想,这是一种长羽毛的恐龙,其化石表明它无法飞行。 羽毛与许多其他进化创新一样,可能只是在最初履行其他功能后才被外适应用于飞行。 这种“外适应”趋势使得预测进化新颖性的出现非常困难。 鸣谢: Emily Willoughby/Stocktrek Images/Getty Images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哲学家卡罗尔·克莱兰 (Carol Cleland) 说,ALife 的努力可能还有另一个致命的缺陷。 她坚持认为,ALife 的构建以理解方法无法增加 N,因为每种产品都基于过于接近地球生命的假设,将其作为其唯一的参考。 另一种起源的尝试可能会捕捉到类生命行为的几个方面,但没有一种可以毫无疑问地活着或从头开始构建的新型生命实例。
克莱兰认为,湿 ALife 的活体创造物是由生物部件组装而成,并使用熟悉的生物化学原理指导,它们不是原始的生命形式,而仅仅是非自然的生命形式。 因此,它们并没有告诉科学家关于生命的其他可能性。“这基本上就像拆开一辆汽车,然后通过用塑料部件替换一些金属部件将其重新组装起来,然后说,‘看,我创造了一辆替代汽车!’” 她说。
硬 ALife 和软 ALife 运行着相反的问题,即与血肉之躯相去甚远。 它们的构建者通常假设生命的定义超越了生物体的物质形式,而是体现在其功能特性中——谁又能说这首先是概括生命的正确策略? 此外,克莱兰认为,总是可以提出对生命的粗略抽象,以至于它无意中包括了一些非生命的例子。 她说,从仅仅 N = 1 就断言自己知道哪些特征是所有生命的关键和普遍特征的科学家的傲慢自大,并不是悲观的狙击,而是一种务实的陈述事实。
“你可以探索已知生命的某些特征,” 克莱兰说。 “但你不能保证这些特征对生命来说是必要的。”
在克莱兰的概念中,硬 ALife 和软 ALife 太抽象,而湿 ALife 又太具体。“你需要介于两者之间的抽象层次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质,” 她说。 大多数 ALifers 都没有忽视弥合这些差距的中间方式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如何从 N 的单个案例中找到它。
救命稻草
如果有人能够重拾对 ALife 研究的信心,也许那就是圣达菲研究所的数学生物学家克里斯·肯佩斯 (Chris Kempes)。 他从生物生命的 N = 1 中提取普遍规律的策略是对地球生物多样性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 大约 40 亿年的开放式进化在生物世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变异,揭示了其成员之间反复出现的关系,并使科学家能够推测共同的约束。
但在查明生命的共同基础时必须谨慎。 天真地看待所有生物生命中都存在的 DNA 并断定它对所有生命都是必要的,这将是天真的。 肯佩斯呼应了克莱兰的担忧,他说,关键是“找到正确的抽象”,既不要太具体也不要太笼统。
为了穿针引线,肯佩斯试图将这些抽象概念与基本的物理原理和量联系起来。 他说,具有物理基础的抽象概念将理所当然地成为生命定律,并且应该在宇宙任何地方的任何 N 中都成立。 这种方法可能会将开放式进化——被诋毁为 ALife 的诅咒——变成它的救星。
肯佩斯和他志同道合的 ALife 同行逻辑上推断出了一些明显的生命约束,例如能量,例如,“因为它是生物体想要做的每件事的预算,” 他说。 科学家们早就知道,生物体的代谢率往往会随着体重的比例增加。 对能量-质量关系的解释范围从维持体温到实现高效的循环系统。 “在这个空间中有一个明确定义的最优值,” 肯佩斯说。 “我认为这是一条生命定律。”
这种能量-质量关系是唾手可得的成果,但普遍理论的其他要素可能不易识别。“我确实认为我们将拥有一个完整的生命理论,尽管我不知道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肯佩斯说。 “我认为该领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生命定律的列表有多长。”
处于起步阶段
ALife 的模糊性质是任何处于起步阶段的科学学科的特征,其从业者认为。“ALife 是前范式的,”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天体生物学家兼理论物理学家萨拉·伊玛丽·沃克 (Sara Imari Walker) 说。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萌芽状态只会增加现在参与 ALife 的紧迫性。 该领域的开放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休耕但肥沃的土壤,可以孕育出可能会蓬勃发展以塑造后代研究的想法。
未定义和不受约束的 ALife 驱动其追随者重新利用旧思想并产生新颖性。 其隐喻“树”的三个分支——硬、软和湿——尚未成长为高耸、发散的高度,这实际上允许任何人在它们之间攀爬。 在这种观点中,像巴特利特这样的科学家和像卢阿普尔这样的 ALife 新手之间合作工作的成果与其说是研究论文,不如说是一次有效的杂交事件,类似于共生物种的进化,它们共同努力以实现共同的生存——也许有一天,甚至能实现统治地位。
当然,这些特征可能根本不令人惊讶或独特。 它们可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复杂性陡峭的进化行为。 最终,ALife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即使这种否定也暗示着某种奇怪的谦卑而又宏伟的东西:也许,就像宇宙中生命本身一样,ALife 的兴起将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