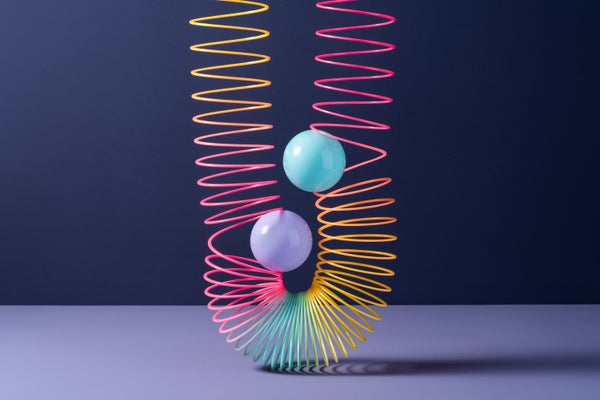万物之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断追问“为什么?”,最终会到达哪里?一神论信仰声称,我们的问题最终必须归结为上帝,一位孤独的、超自然的创造者。物理学家对这一假设不满意,他们假设一切都源于单一的原始力或粒子,也许是超对称弦,我们堕落世界中无数的力和粒子都从中流出。
请注意,尽管宗教和物理学存在诸多差异,但它们都抱有超还原论的信念,即现实归根结底是一个东西。称之为“一元论教条”。在过去的40年里,我一直怀有对一元论教条并非完全理性的厌恶,原因我将在下文揭示。因此,我对以下猜想很感兴趣:在现实的核心,至少有两个东西在相互作用。换句话说,存在着一种互动,一种关系。称之为“关系论教条”。
极富创造力的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是这一概念的早期探索者。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信息、物理、量子:寻找联系》中,惠勒试图解答“古老的问题:存在是如何产生的?”他推测,答案可能来自物理学和信息论的融合。前者关注“物”(its),即物理事物,后者关注“比特”(bits),定义为对是非问题的回答。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思想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惠勒提出,“每一个物理量,每一个‘物’,都从比特,即二进制的是非指示中获得其最终意义,我们用‘比特生万物’(it from bit)这句话来概括这一结论。”惠勒注意到测量在量子实验结果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参与性宇宙”中,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把世界带入存在,反之亦然。
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延续了惠勒的观点,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关系量子力学》中,他认为量子力学破坏了“朴素实在论”,即科学发现的现实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观察而存在的观点。他提出了他称之为量子力学的“关系”解释,该解释认为事物只存在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罗韦利指出,伽利略和康德等人预见了关系视角。
罗韦利继续阐述关系论教条。在即将发表在《意识研究杂志》上的一本关于泛心论的论文集中,他写道:“20世纪的物理学不是关于个体实体自身如何存在。它是关于实体如何向彼此显现。它是关于关系的。”罗韦利认为,这种观点不仅适用于电子和光子,而且适用于所有的现实,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不足以解释石头、雷暴和思想。”
惠勒和罗韦利在早期的论文中都没有引用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但他们本可以这样做。在他独具一格的1979年著作《哥德尔、埃舍尔、巴赫》中,霍夫施塔特深入探讨了心灵和物质最深层的奥秘。与惠勒和罗韦利一样,研究物理学的霍夫施塔特也认为,粒子只有通过与其他粒子的相互作用才能获得属性。但正如他的书名所示,霍夫施塔特在他的解释世界的努力中远远超出了物理学的范畴,借鉴了数学、计算机科学、遗传学、音乐和艺术。
我会说,霍夫施塔特痴迷于指涉自身、谈论自身或以其他方式与自身互动的事物——尤其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这是一个关于证明局限性的证明。霍夫施塔特提出,意识、自我、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都源于“奇异循环”,即那些把自己带入存在的事物。艺术家M.C.埃舍尔在他的著名画作《画手的两只手》中提供了一个奇异循环的醒目图像。
另一位雄辩的关系论教条阐释者是科学作家阿曼达·盖弗特。在去年12月听完她的演讲后,我为我的播客节目“身心问题”采访了盖弗特。盖弗特似乎致力于超越旧的二元对立,比如心灵和物质之间的二元对立。她对严格的唯物主义(它规定物质是根本的)和唯心主义(它坚持心灵先于物质)都不满意。“量子力学的核心教训,”盖弗特告诉我,“是‘主体和客体永远无法分离’。”
盖弗特从各种来源汲取灵感,包括惠勒和哲学家马丁·布伯,经典著作《我与你》的作者。她还对QBism(有时称为量子贝叶斯主义)很感兴趣,这是一种量子力学的解释,与惠勒和罗韦利的解释有重叠之处。根据QBism,我们每个人都通过与世界的互动创造了自己的个人世界;客观的、共识的现实从我们所有主观世界的互动中产生。
也许,盖弗特推测,我们既不是生活在第一人称世界,也不是生活在第三人称世界,正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所暗示的那样。也许我们生活在第二人称世界,而存在的基本实体不是“我”或“它”,而是“你”。“第二人称总是处理关系,”盖弗特解释说,因为每一个“你”都意味着一个“我”与“你”互动。盖弗特说,这种观点“绝对不是唯物主义,但也不是唯心主义”。
我的一部分发现关系论教条,尤其是盖弗特以“你”为中心的形而上学,是美好的和令人安慰的,是唯物主义的受欢迎的替代品。关系论教条似乎也符合直觉。正如词语必须由其他词语来定义一样,我们人类也是由其他人来定义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带入存在的。否则怎么可能呢?
此外,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我对一元论教条长期以来一直感到厌恶。这种反感可以追溯到1981年的一次迷幻药体验,在那次体验中,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孤独的意识,宇宙中唯一的意识。除了我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起初,这个启示让我兴奋,但后来它把我吓坏了。我感到非常痛苦,非常孤独。这种情绪伴随着一种奇怪的智力潜台词。我想:一个东西和什么都没有之间有什么区别?一个东西只有在与另一个东西的关系中才存在。如果我是唯一存在的东西,我可能还不如不存在。
一次非常好的旅行变成了一次非常糟糕的旅行,负面影响挥之不去;唯我论不再只是一种有趣的幻想,而是一种可怕的可能性。从那时起,我就对一元论教条持怀疑态度,无论它来自神秘主义还是科学。我担心一元论教条是真的——一个单一的心灵是万物的基础——但我不希望它是真的。因此,我被关系论教条所吸引。
然而,我对关系论教条持怀疑态度,就像我对所有特权化心灵、意识、观察、信息的形而上学体系一样。它们带有自恋、拟人化和一厢情愿的色彩。这就是为什么我嘲笑以心灵为中心的理论为新地心说,这是对中世纪认为宇宙围绕我们旋转的信念的倒退。特别是关系论教条,让我想起了“上帝就是爱”这句感伤的口号。
老实说,我对所有终极理论都持怀疑态度,无论是基于一元论、关系、奇异循环还是其他原则。约翰·惠勒在他1989年关于比特生万物的文章结尾时,用一句令人振奋的惊叹,几乎是一句祈祷。“当然,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将掌握这一切的中心思想,它是如此简单、如此美好、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我们都会对彼此说,‘哦,怎么可能是其他的呢!我们怎么可能都如此盲目如此之久!’”
我曾经和惠勒一样渴望一种如此强大的启示,以至于它会驱散存在的怪异性。现在我害怕这种顿悟。如果我们确信我们已经弄清楚了一切,那么我们的创造性努力——无论是科学的、艺术的、精神的还是政治的——都可能僵化。幸运的是,我对人类的好奇心和不安分抱有信心。我的希望和期望是,世界将永远让我们猜测下去。
延伸阅读:
我在我的两本最新著作中深入探讨了各种棘手的关系问题:《注意:性、死亡和科学》和《身心问题:科学、主观性和我们真正的身份》。
另请参阅我的播客节目“身心问题”,我在节目中与阿曼达·盖弗特和其他痴迷于存在之谜的专家进行了对话。
这是一篇观点和分析文章;作者或多位作者表达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大众科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