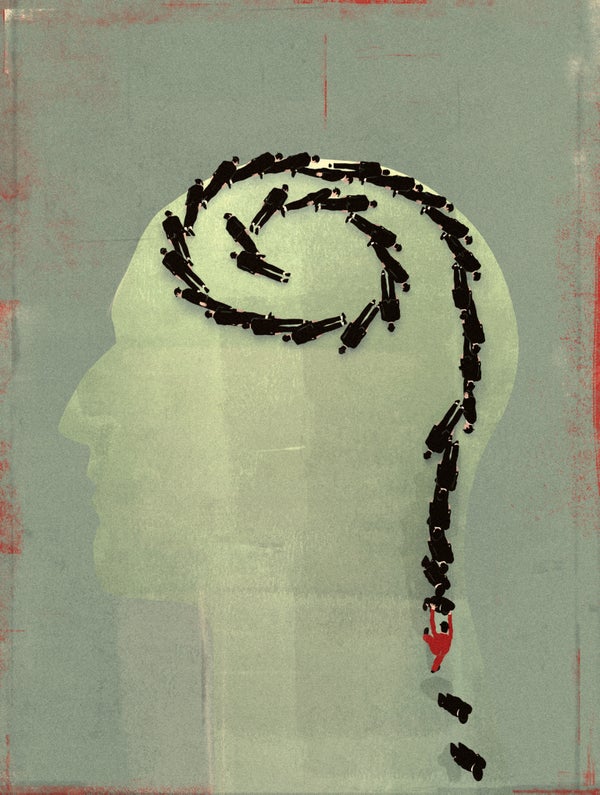15年来,英国保险公司同意不使用潜在投保人的基因信息来确定某些人寿保险的资格。这项延期偿付有一个关键例外。保险商在撰写某些保单时,可以考虑一个人是否携带这种疾病的基因,这种疾病曾经被称为慢性遗传性舞蹈病,现在简称为亨廷顿舞蹈症。
意识到基因检测呈阳性后,保险公司就知道,在持续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申请人的死因很可能是亨廷顿舞蹈症——这种知识比他们通常考虑的其他因素(如吸烟、饮酒或骑摩托车)更具确定性。携带错误基因的人可能在壮年时期就开始经历情绪波动和记忆障碍,通常在 30 岁到 50 岁之间,尽管这些变化可能发生在较晚的时候。然后症状会恶化,扩大到包括无法控制的运动和痉挛,以及不稳的步态,通常被描述为蹒跚的“舞蹈”。身体会一点一点地失去所有功能,逐渐减慢速度,直到完全不动,这个人最终会屈服于疾病。
研究人员多年来已经了解到,一种被称为huntingtin基因的异常会导致这种疾病。所有人都会携带huntingtin基因,因为它在出生前神经系统的发育中非常重要。但这种基因在人与人之间略有不同,这些差异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会生病,而另一些人则保持健康。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方式是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当今塑造我们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基因的一个部分包含一个核苷酸三联体,或“DNA 代码字母”——即 C-A-G——连续重复多次。在保持健康的人中,CAG 三联体的数量在 8 到 35 之间。如果数量更高,个体最终会患上这种疾病,这种疾病以首次描述它的医生乔治·亨廷顿(George Huntington,1850-1916 年)的名字命名。一个坏基因副本(我们每个人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两个huntingtin基因之一)足以引起这种疾病,并且受影响父母的每个孩子都有很高的机会(50%)携带该基因。由于这种遗传模式,欧洲和美洲每 10,000 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研究人员也已经知道,亨廷顿舞蹈症的症状是由于纹状体和大脑皮层(控制身体运动和高级认知功能的大脑区域)中的神经元死亡造成的。因此,对这种疾病的大量研究旨在确定高重复版本的基因如何造成这种损害,并开发可以阻止症状无情进展的药物。
我们的实验室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实验室都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开展这些工作。几年前,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对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为什么有害版本的基因会代代相传,而不是被自然选择淘汰。我们想知道是否有一种生物学上的冒险游戏在起作用。对于我们的物种来说,拥有大量但也许不是太多的基因重复序列,是否有一些生存或繁殖益处?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也会问这个问题;他们明白答案可能不会治愈任何人,但他们仍然想知道。
最近,对这个谜题的调查已经对该基因在人类和其他生物神经系统发育中的作用产生了有趣的见解。事实证明,CAG 重复序列数量的增加似乎可以促进神经元的功能,只要增加不超过疾病阈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廷顿舞蹈症与其说是一种遗传疾病,不如说是一种塑造大脑的进化过程出错的不幸副产品。一种可能让我们“更聪明”的基因变化,如果推得太远,似乎会导致悲惨的后果。这就是亨廷顿舞蹈症的悖论所在。
在开始之初
为了让我们当前理解该基因在神经系统进化中所起的作用,侦探工作需要研究人员回顾超过十亿年前,追溯到人类和一种称为盘基网柄菌的多细胞变形虫的祖先出现之时。这些早期生命形式生活在古元古代和中元古代之间,是第一个携带该基因的生物,尽管其形式与人类版本略有不同。
盘基网柄菌变形虫的后代仍然可以在森林地面和腐烂的树叶中找到,以细菌为食。它们让当时在柏林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的米格尔·安德拉德-纳瓦罗及其研究小组能够在 2009 年搜索复杂的数据库并在变形虫中找到该基因。安德拉德-纳瓦罗及其合作者发现,变形虫的亨廷顿基因(huntingtin的非正式名称)与人类基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包含 CAG 三联体。然而,该基因似乎在该生物生命的一个阶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让单细胞变形虫与其他变形虫结合,形成一个称为假菌柄体的多细胞实体。
当食物稀缺或环境条件恶劣时,这种变形虫的集合体比单个变形虫更能自卫。2011 年,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迈克尔·迈尔和詹姆斯·古塞拉报告说,该基因调节许多重要的细胞过程,包括盘基网柄菌向多细胞阶段的转变。缺乏亨廷顿基因的单个细胞移动困难,并且无法与其他细胞正常聚集。因此,该基因似乎是需要彼此“社交”才能生存的细胞的关键。
事实上,该基因具有许多功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团队发现,它控制着变形虫的繁殖时间,并调节它们对周围环境刺激的反应,这些刺激促使它们向食物移动。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我们发现盘基网柄菌版本的基因可以保护哺乳动物细胞免受触发细胞死亡的刺激。
变形虫先于生命树在 5.5 亿多年前分裂成两个分支:原口动物(包括昆虫、甲壳类动物、软体动物)和后口动物(导致了第一批脊椎动物——鱼类、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和现代人类)。只有后口动物继续在基因中人类致病突变的位置积累 CAG 三联体。
正如我们在 2008 年发现的那样,亨廷顿基因开始在称为棘皮动物(例如海胆Strongylocentrotus purpuratus)的基部后口动物类别中获得 CAG 三联体。我们与米兰大学的一组专门从事生物计算技术的科学家合作,破译了海胆基因的 DNA 序列,在基因的初始部分识别出两个 CAG 三联体。
在这种生物中,DNA 序列仍然与人类基因的 DNA 序列不同。尽管海胆具有原始的神经系统,但该基因主要存在于非神经组织中。它的缺失表明,在进化早期,该基因及其两个 CAG 三联体在神经系统中没有重要功能。对原口动物三联体的研究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但很明显,它们仅极少出现(例如,蜜蜂具有单个 CAG)。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动物门类在其亨廷顿基因中不携带任何 CAG。
在 2000 年代后期,我们的实验室分析了其他后口动物的亨廷顿基因中的 DNA 序列——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头索纲(我们与意大利热那亚大学的马里奥·佩斯塔里诺小组合作完成)的文昌鱼或矛形文昌鱼的序列。文昌鱼(一种小型鱼类生物)的生物学标志着神经系统进化中的一个关键发展——获得了从动物前端延伸到后端的极化神经结构。文昌鱼神经索的前端略有分化,形成一个囊泡,这似乎是原始大脑的早期前体。
序列显示,与海胆一样,两个 CAG 三联体一起出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体对周围的遗传字母序列与包括人类在内的脊椎动物相似,并且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主要局限于神经组织,这让我们推测这种差异可能有助于形成原始大脑及其前后结构。
点击或轻触放大

图表作者:阿曼达·蒙塔内斯
当研究人员随后检查脊椎动物的基因组时,他们发现 CAG 三联体开始在神经系统更复杂的生物体中明显延长,直到它们在人类中达到最大延伸。可以通过查看与人类越来越远的物种来推断这一点,例如牛(15 个 CAG)、猪(18 个)、狗(10 个)、小鼠(7 个)和负鼠(6 个)。许多生物体,包括灵长类动物,具有 CAG 片段,其长度在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有所不同。
脊椎动物标志着神经进化的新篇章。它们的大脑是从胚胎中形成的中空结构(称为神经管)发育而来的,神经管后来发育成大脑。1997 年,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马西·麦克唐纳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亨廷顿基因参与神经管的形成,2012 年,我们的团队证实并扩展了这一发现,表明它有助于培养皿中类似神经管结构的形成。
人类三联体
与此同时,其他研究方向开始勾勒出 CAG 重复序列的另一个作用:改善思维。这些发现部分源于 1970 年代开始的寻找该基因的努力。最终,在 1993 年,遗传学家南希·韦克斯勒和其他 57 位研究人员(均来自亨廷顿舞蹈症合作研究小组)分离并测序了位于 4 号染色体上的人类基因,从而为发现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 CAG 三联体数量为 36 个或更多铺平了道路。
一年后,现任剑桥大学遗传学家的戴维·C·鲁宾斯坦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健康个体亨廷顿基因中的 CAG 部分在传递给后代时有扩张的趋势。同样在 1994 年,剑桥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佩鲁茨发现谷氨酰胺(由 CAG 遗传字母编码的氨基酸或蛋白质构建块)促进与其他蛋白质的结合。然而,这些结果之后是关于 CAG 重复序列的非病理性功能研究的长期停滞期。当时,CAG 和其他重复序列被视为遗传“垃圾”,可能没有任何用途。
2008 年,现任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的约翰·W·方登三世和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的戴维·金通过推测三联体核苷酸可能参与神经系统的发育和进化,以及脑细胞中 CAG 三联体的扩张可能增强认知能力以及性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互动,为这个问题注入了新的兴趣。
从那时起,实验证据越来越多地支持这些推测。根据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迈克尔·海登团队进行的一项研究,每 17 个人中就有 1 人携带“中间等位基因”——一种健康的亨廷顿基因,其 CAG 总数在 27 到 35 个重复序列之间,这是一个高但非病理性的数字。CAG 三联体数量多的健康人在苍白球(控制运动计划和控制并参与更高层次认知功能的大脑区域)中往往有更多的灰质(神经元)。在脑细胞的培养皿研究中,我们的实验室也表明,三联体越多,神经系统样结构就越复杂[参见上方框]。
即使是注定会患病的基因携带者也表现出高水平的认知功能。2012 年,当时都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的卡斯滕·萨夫特和克里斯蒂安·贝斯特报告说,那些携带导致疾病的基因变异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在视觉和其他知觉测试中比携带正常变异的人获得更好的分数。
大脑助手
关于亨廷顿基因的新研究也深入探讨了该基因在大脑中执行哪些特定任务。在我们使用培养皿中脑细胞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该基因的健康形式使神经元更强壮,更能抵抗压力。相反,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关闭小鼠大脑中的该基因会导致细胞死亡,并出现类似于携带有害版本亨廷顿基因的小鼠的神经系统症状。我们还证明,该基因刺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产生,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是一种促进大脑回路形成和神经信号传递的蛋白质。
也许最重要的是,亨廷顿基因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处于最活跃状态。很简单,没有它,我们就不会出生。该基因在原肠胚形成过程中开始工作,原肠胚形成是胚胎发育的主要身体组织发育的阶段。稍后,该基因调节新神经元的形成并帮助连接它们。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亨廷顿舞蹈症的悖论仍然存在。获得不断延伸自身的 CAG 序列可能是亨廷顿基因的主要进化成就,但扩张的趋势也带来了毁灭性疾病的可怕风险。围绕该基因重复遗传片段的谜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困扰神经科学家。我们仍然需要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该基因中的 CAG 三联体长度差异如此之大。当 CAG 三联体的数量接近会导致亨廷顿舞蹈症诊断的阈值时,大脑会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该基因在重复 36 次后突然变得有害?理解亨廷顿基因既是一种恩惠,也是一种祸害,可能有助于减轻该疾病的一些污名,使其不被视为一种基因缺陷,而是最终使我们成为人类的生物学过程的副产品。
进化遗产
一项实验加速了数百万年的进化
我们从最近的实验中了解到,亨廷顿基因中的 CAG 重复序列似乎影响了脊椎动物神经系统的进化方式,并且更多的三联体使更精细的早期生命发育过程得以发生。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研究了该基因对称为神经玫瑰花环的结构的影响,这种结构是在实验室培养皿中培养胚胎细胞时产生的。我们通过使用从早期小鼠胚胎中提取的干细胞重新创建了该过程。这些胚胎干细胞具有分化成其他细胞类型的能力。如果干细胞用已知可以指导神经系统发育的分子处理,它们就会变成所谓的神经上皮细胞,这些细胞围绕中心腔排列成类似于花朵的图案——神经玫瑰花环。这些玫瑰花环模拟了胚胎中神经管的发育,神经管是中枢神经系统形成的结构。
首先,我们证明了亨廷顿基因对玫瑰花环很重要。我们发现它允许玫瑰花环中的细胞相互粘附。缺乏健康亨廷顿基因的干细胞没有形成花状结构。事实上,在没有健康基因的情况下,一种酶会切割细胞膜上的粘附蛋白,阻止细胞附着。如果亨廷顿基因得到恢复,玫瑰花环就会开始形成。
接下来,我们询问,如果我们从小鼠干细胞中去除原始基因,并用来自变形虫(无 CAG)、文昌鱼(两个)、鱼(四个)和人类(15 个)等的基因替换它,会发生什么?玫瑰花环发育的差异表明,逐渐增加的 CAG 重复序列数量是否可能使亨廷顿基因更能够帮助这些物种的神经系统形成。
变形虫等不太复杂物种的基因没有产生玫瑰花环。第一个可识别的结构(尽管不完整)是在插入文昌鱼基因后出现的。一般来说,具有更多 CAG 的基因导致形成更好且更大的玫瑰花环,并具有较大的中心腔。来自鱼类的亨廷顿基因诱导了美丽的玫瑰花环的形成——比文昌鱼基因诱导的玫瑰花环更大、由更多细胞组成的结构。人类基因(重复序列数量最多的基因)产生了最佳结果,具有最大和结构最佳的玫瑰花环。
这些结果共同提供了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概要。——C.Z. 和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