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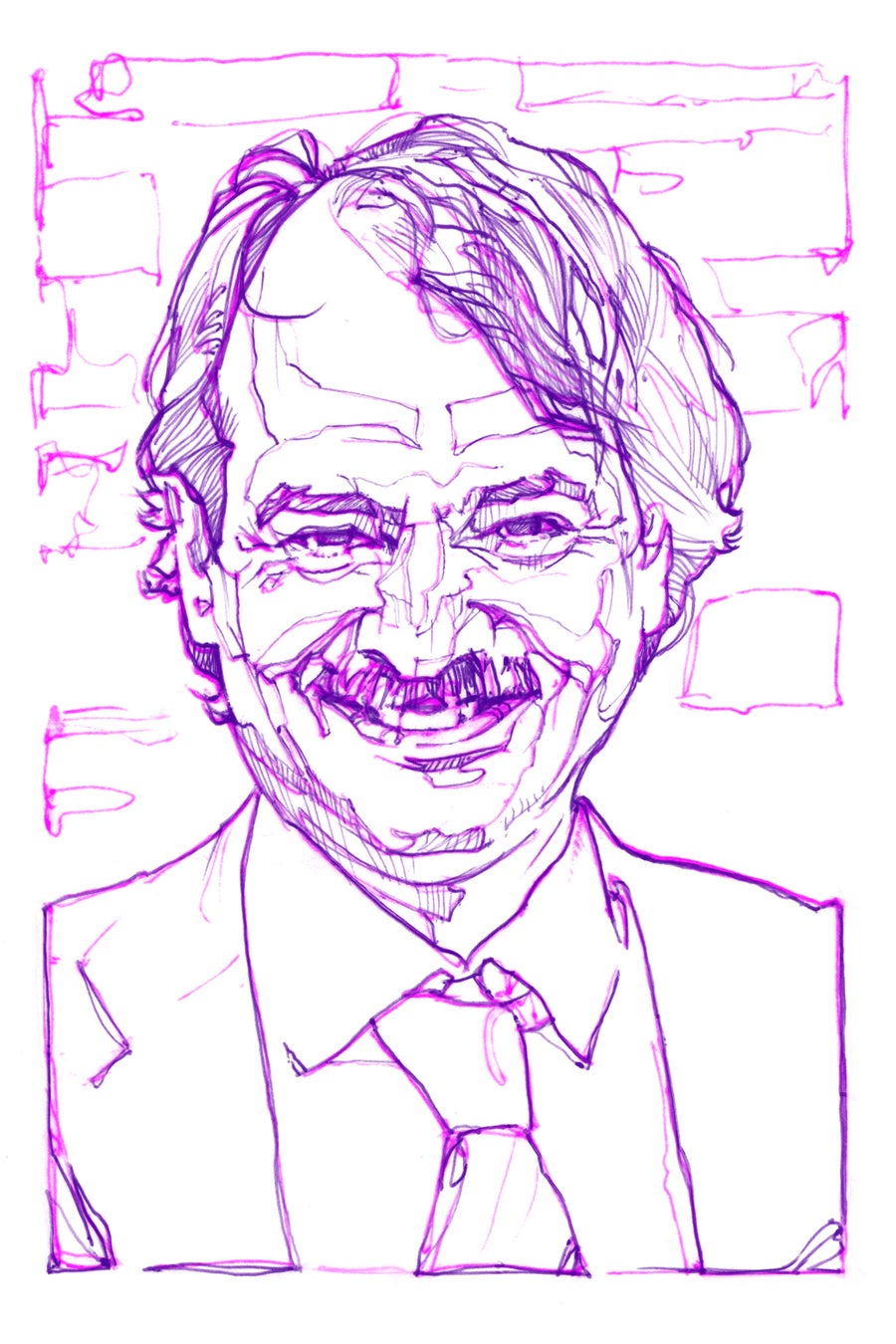
约翰·P·A·伊奥安尼迪斯,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由布鲁克·博雷尔讲述。图片来源:巴德·库克
关于人类生命问题的答案并非像测量石头在多少秒内落到地面那样确定的事物。如果它是确定的,那可能就不是生命了。那会是一块石头。在生物医学领域内,找出某种效应是否真实是很棘手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标准。并非所有工具都适用于每个问题,而且对于我们在开始研究之前所知道的内容,复杂程度也各不相同。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将帮助确保关于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思想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尽管如此,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核心维度是在一项新的研究中,复制首次调查中观察到的结果的能力。多年来,在该领域,我们一直不鼓励这样做。为什么要浪费钱去做你以前做过的事情,更不用说别人以前做过的事情了?但是许多研究人员意识到,不可能忽略重复研究。
但是,为了使重复研究有效,必须对原始研究的完成方式进行详细的解释。你需要说明书、原始数据,甚至可能是一些定制的计算机软件。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不愿意分享这些信息,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科学是一项集体努力,我们应该默认保持开放和分享。
历史语言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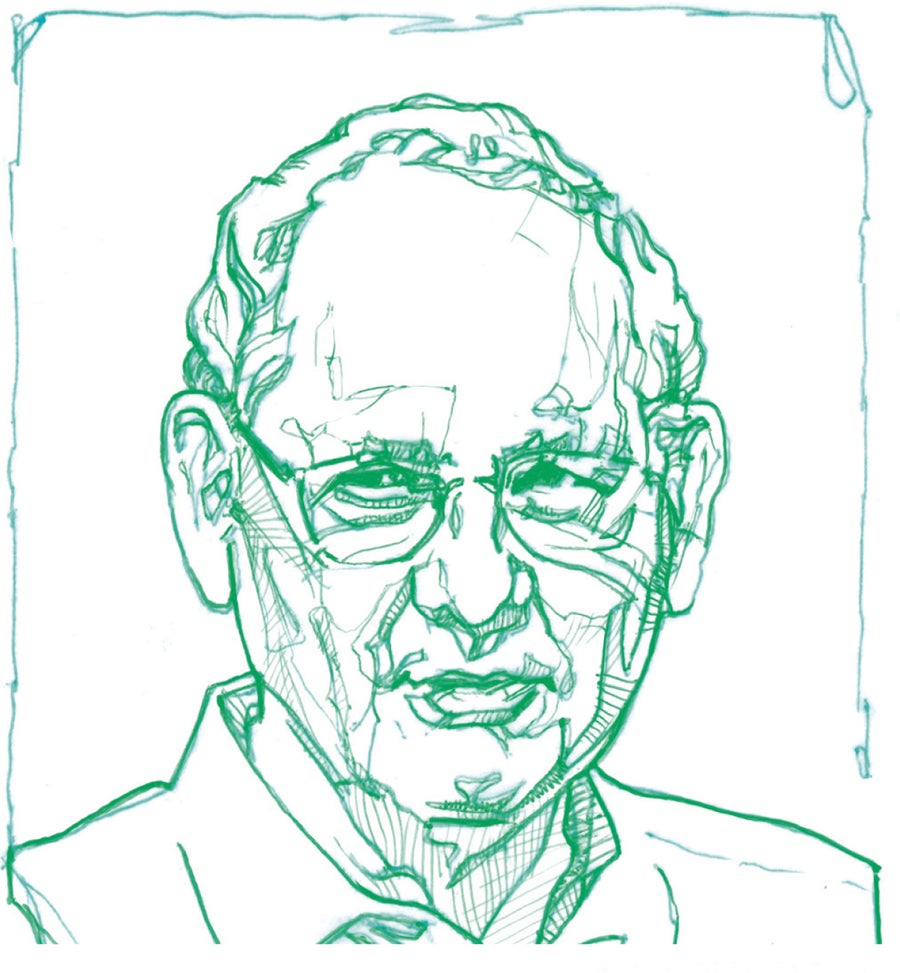
莱尔·坎贝尔,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由布鲁克·博雷尔讲述。图片来源:巴德·库克
像任何科学家一样,语言学家也依赖科学方法。语言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描述和分析语言,以发现人类语言中可能和不可能的全部范围。由此,语言学家旨在通过人类语言能力来实现他们理解人类认知的目标。
因此,描述濒危语言、在它们仍在被使用时记录它们、确定语言学上可能的全部范围的工作迫在眉睫。已知的人类语言约有 6,500 种;其中约 45% 处于濒危状态。
语言学家使用一套特定的标准来识别濒危语言,并确定一种语言的濒危程度:儿童是否仍在学习这种语言?有多少人说这种语言?说这种语言的人口比例是否相对于更广泛的人口而言正在下降?以及使用该语言的语境是否正在减少?
科学客观性和“真理”的问题与濒危语言研究有关。“真理”在某种程度上是情境性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获得更多数据和证据或我们的方法改进时,我们认为真实的事物可能会改变。对濒危语言的调查经常会发现我们以前不知道在语言中可能存在的事物,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之前关于人类语言限制的主张,因此有时我们认为真实的事物可能会发生转变。
古生物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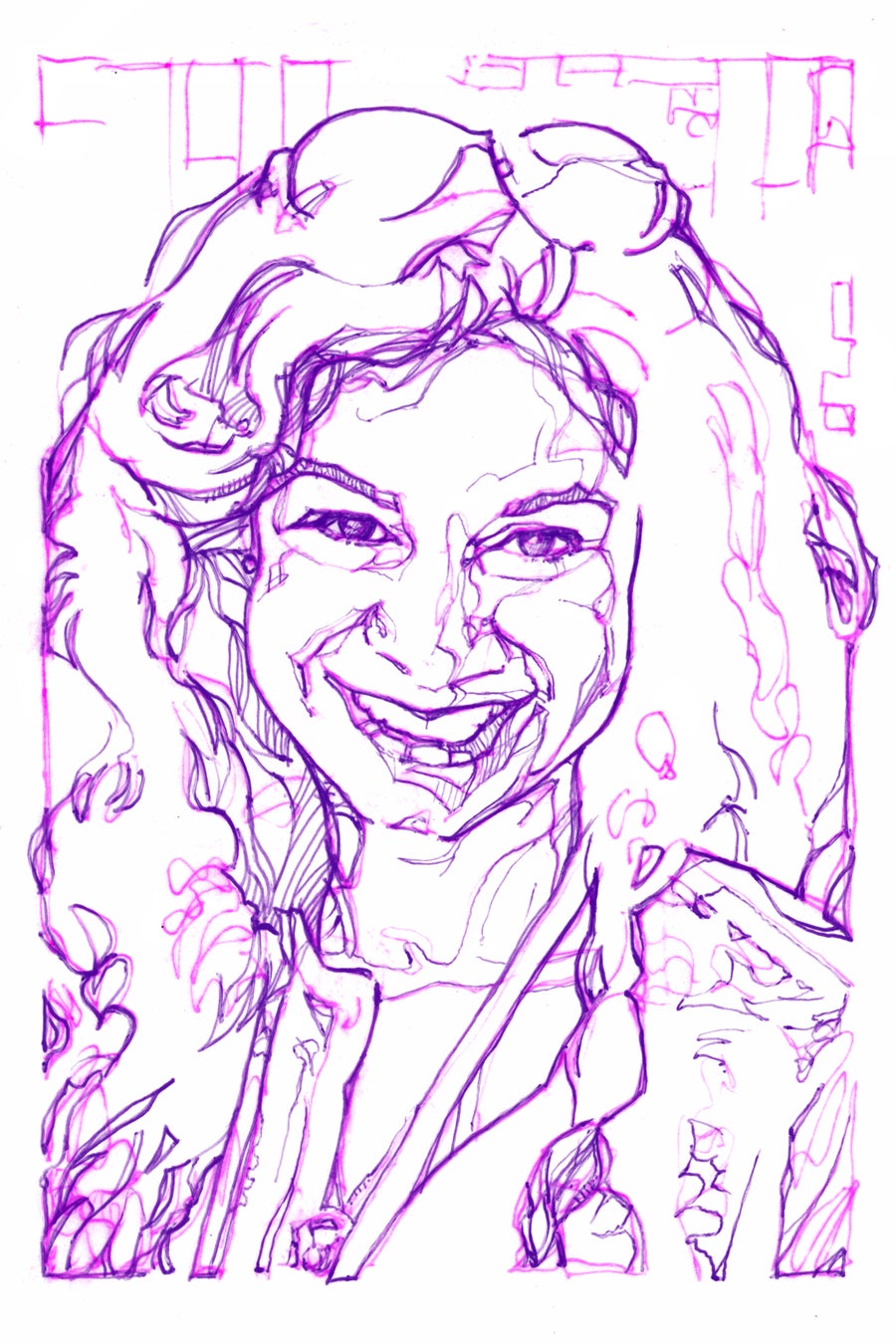
安贾莉·戈斯瓦米,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教授和研究负责人,由布鲁克·博雷尔讲述。图片来源:巴德·库克
我们在古生物学中真理的基本单位是化石——过去生命的清晰记录——我们还使用来自活生物体的遗传证据来帮助我们将化石放入生命之树中。它们共同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生物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关的。因为我们正在观察存在于更广泛生态系统中的已灭绝动物,所以我们从其他领域获取信息:周围岩石的化学分析以了解化石的年代,当时世界陆地可能在哪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环境变化等等。
为了发现化石,我们仔细搜索地貌,在岩石中找到它们。你可以通过化石的形状和内部结构来区分化石和任何旧岩石。例如,一块化石骨头会有称为骨单位的微小圆柱体,血液血管曾经从中穿过骨头。有些化石很明显:恐龙的腿,巨大的、完整的骨头。较小的碎片也可能说明问题。对于我研究的哺乳动物来说,你可以从一颗牙齿的形状中看出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将这些信息与遗传学相结合,通过使用来自我们认为与化石相关的活生物体的DNA样本,这基于解剖结构和其他线索。
我们进行这些调查不仅是为了重建过去的世界,也是为了看看它们能告诉我们关于我们当前世界的什么。例如,5500 万年前,气温曾出现大幅飙升。这与今天的情况截然不同,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了那个时代的动植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进行比较,看看相关的生物可能会如何应对当前的气候变化。
社会技术专家

凯特·克劳福德,纽约大学杰出研究教授,纽约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大众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由布鲁克·博雷尔讲述。图片来源:巴德·库克
机器学习领域面临的最大认识论问题是:我们测试假设的能力是什么?算法学习从大量的例子中检测模式和细节——例如,一个算法在看到数千张猫的照片后可以学习识别猫。在我们获得更高的可解释性之前,我们可以通过算法的结论来测试结果是如何实现的。这引发了一种幽灵,即我们对深度学习系统的结果没有真正的问责制——更不用说它们对社会机构的影响时应有的正当程序了。这些问题是该领域正在进行的辩论的一部分。
此外,机器学习是否代表着对科学方法的一种拒绝,科学方法旨在不仅找到相关性,还要找到因果关系?在许多机器学习研究中,相关性已成为新的信仰,而以因果关系为代价。这引发了关于可验证性的真正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正在倒退。我们在机器视觉和情感识别领域看到了这一点。这些系统从人的照片中推断出他们的种族、性别、性取向或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这些方法在科学和伦理上都令人担忧——带有颅相学和面相学的回声。对相关性的关注应该引起对我们声称人的身份的能力的深刻怀疑。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强烈的声明,但鉴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这不应该引起争议。
统计学家

妮可·拉扎尔,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统计学教授,由布鲁克·博雷尔讲述。图片来源:巴德·库克
在统计学中,我们通常看不到整个宇宙,而只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通常是一小部分,这部分可能讲述一个与另一小部分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们试图从这些小部分飞跃到更大的真理。很多人将真理的基本单位视为 p 值,这是一种统计度量,衡量如果我们对更大宇宙的假设成立,我们在我们的小部分中看到的东西有多么令人惊讶。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
实际上,统计显著性的概念是基于应用于 p 值的任意阈值,它可能与实质性或科学意义几乎无关。太容易陷入一种思想模式,为该任意阈值赋予意义——它给了我们一种虚假的确定感。而且,在 p 值背后隐藏许多科学罪恶也太容易了。
加强 p 值的一种方法是将文化转向透明化。如果我们不仅报告 p 值,还展示我们如何得到它的工作——例如,标准误差、标准偏差或其他不确定性度量——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数字的含义。我们发布的信息越多,就越难隐藏在 p 值背后。我们是否能达到那个目标,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
数据记者

梅雷迪思·布鲁萨德,纽约大学亚瑟·L·卡特新闻学院副教授,由布鲁克·博雷尔讲述。图片来源:巴德·库克
人们认为,因为有数据,所以数据一定是真实的。但事实是,所有数据都是脏的。人创造数据,这意味着数据像人一样有缺陷。数据记者所做的一件事是质疑真理的假设,这起到重要的问责作用——一种权力制衡,以确保我们不会集体被数据冲昏头脑并做出糟糕的社会决策。
为了质疑数据,你必须做大量的清洁工作。你必须清理和组织它们;你必须检查数学。而且你还必须承认不确定性。如果你是科学家,并且你没有数据,你就写不出论文。但作为一名数据记者,最棒的事情之一是稀疏的数据不会阻止我们——有时缺乏数据告诉我的东西同样有趣。作为一名记者,我可以使用文字,文字是交流不确定性的绝妙工具。
行为科学家

菲利普·阿提巴·高夫,耶鲁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和心理学教授,警察公平中心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由布鲁克·博雷尔讲述。图片来源:巴德·库克
你在实验室科学中拥有的控制比在行为科学中要严格得多——在人身上检测小效应的能力远低于化学等学科。不仅如此,人们的行为会随着时间和文化而变化。当我们思考行为科学中的真理时,真正重要的是不仅要直接重复一项研究,还要将重复扩展到更多的情况——实地研究、相关性研究、纵向研究。
那么我们如何衡量种族主义呢?种族主义不是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结果模式——一个整个人们受压迫的系统?最好的方法是观察行为模式,然后看看当我们改变或控制一个变量时会发生什么。模式会如何变化?以警察执法为例。如果我们从等式中消除偏见,种族差异模式仍然存在。贫困、教育和我们认为可以预测犯罪的许多事物也是如此。它们都不足以解释种族差异化的警察执法结果模式。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因为这不像我们不知道如何产生非暴力和公平的警察执法。看看郊区就知道了。我们已经在那里做了几代人了。
当然,存在不确定性。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我们远未对因果关系充满信心。我们作为科学家的责任是描述这些不确定性,因为对种族主义等事物的驱动因素的错误计算是制定正确政策和制定错误政策之间的区别。
神经科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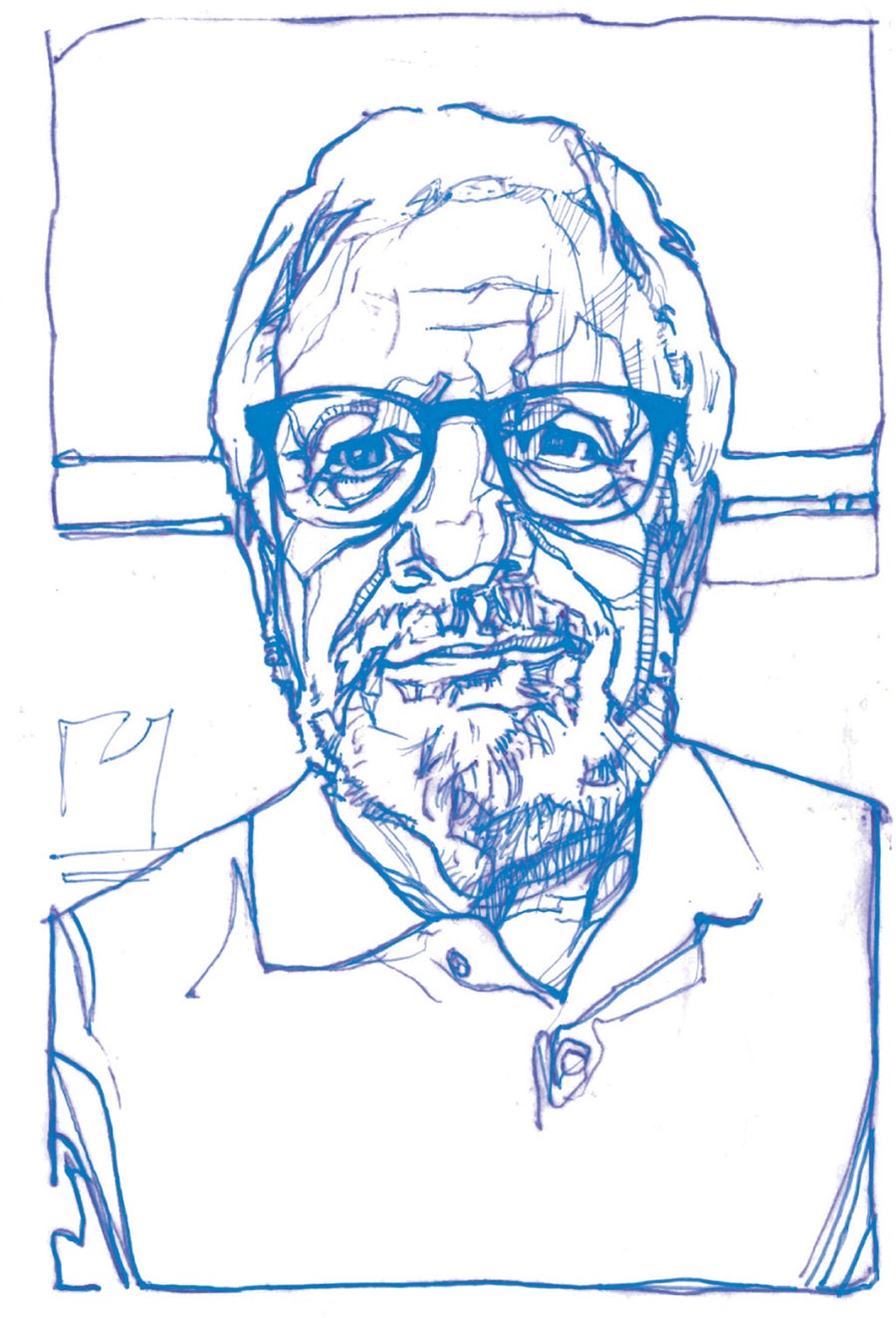
斯图尔特·费尔斯坦,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由布鲁克·博雷尔讲述。图片来源:巴德·库克
科学并不像许多人可能认为的那样寻找真理。相反,科学的真正目的是寻找更好的问题。我们进行实验是因为我们对某些事情一无所知,并想了解更多,有时这些实验会失败。但我们从无知和失败中学到的东西会开启新的问题和新的不确定性。而这些是更好的问题和更好的不确定性,它们会引导我们进行新的实验。如此循环往复。
以我的领域神经生物学为例。大约 50 年来,感觉系统的基本问题一直是:什么信息被发送到大脑?例如,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的大脑什么?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想法发生了逆转:大脑实际上是在向感觉系统提出问题。大脑可能不仅仅是在筛选来自眼睛的大量视觉信息;相反,它是在要求眼睛寻找特定的信息。
在科学中,总是存在未完成的事情和小小的死胡同。虽然你可能认为你已经清理了一切,但总会有新的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价值在于不确定性。它不应该引起焦虑。它是一个机会。
理论物理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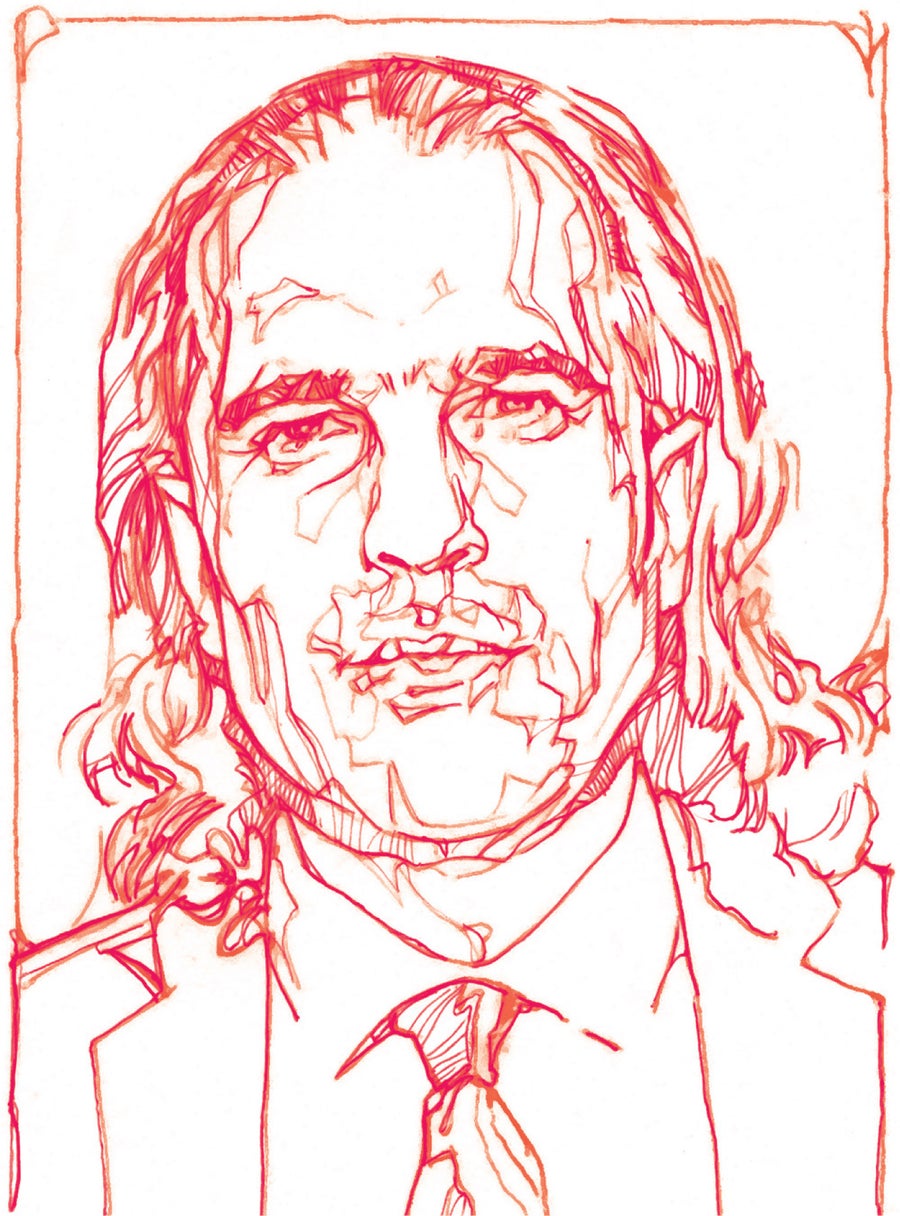
尼玛·阿卡尼-哈米德,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自然科学学院教授,由布鲁克·博雷尔讲述。图片来源:巴德·库克
物理学是最成熟的科学,物理学家对真理这个主题非常执着。那里存在一个真实的宇宙。中心奇迹是存在简单的基本定律,以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可以描述它。也就是说,物理学家不从事确定性,而是从事置信度。我们吸取了教训:纵观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我们认为对现实的最终描述至关重要的一些原则并不完全正确。
为了弄清楚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有理论并建立实验来检验它们。从历史上看,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例如,物理学家在 1964 年预测了希格斯玻色粒子的存在,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构建了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并在 2012 年发现了希格斯的物理证据。有时我们无法构建实验——它太庞大或太昂贵,或者以现有技术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尝试思想实验,从现有数学定律和实验数据的现有基础设施中提取思想。
这里有一个例子:时空概念自 20 世纪初以来已被接受。但要观察更小的空间,你必须使用更强大的分辨率。这就是为什么大型强子对撞机周长 17 英里的原因——产生探测粒子之间微小距离所需的巨大能量。但在某个时刻,会发生一些糟糕的事情。你将释放如此巨大的能量来观察如此小的空间,以至于你实际上会创建一个黑洞。你试图看到内部是什么使它无法做到,而时空的概念崩溃了。
在历史的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理解世界的某些方面,但并非所有方面。当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带来更大的图景时,我们必须重新配置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旧事物仍然是真理的一部分,但必须旋转并以新的方式放回更大的图景中。
本文最初以侧边栏系列的形式发表在大众科学第 321 卷,第 3 期(2019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