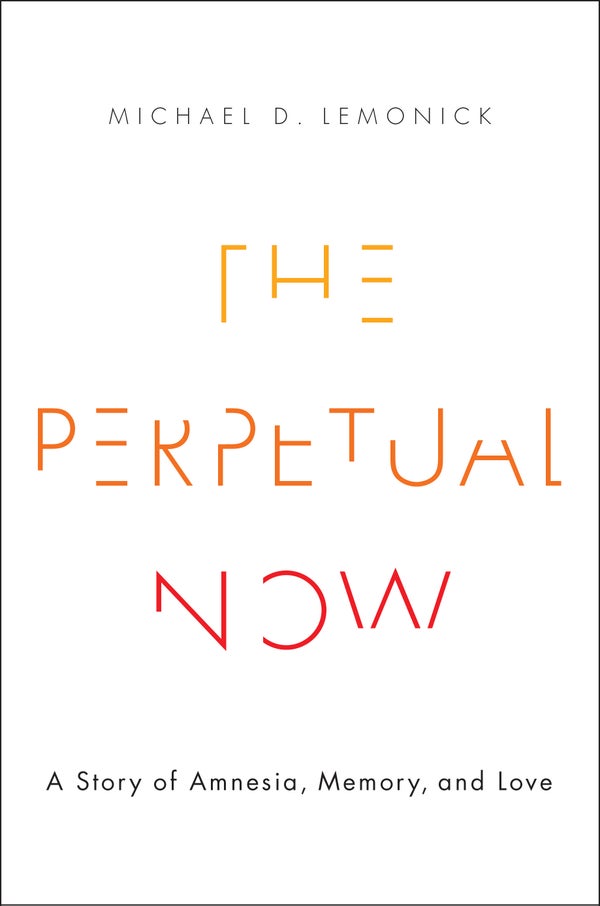节选自《永恒的当下:关于失忆症、记忆和爱的故事》,作者:迈克尔·D·莱蒙尼克。经Doubleday安排出版,Doubleday是Penguin Random House, LLC旗下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集团的一个分支。版权 © 2017 迈克尔·D·莱蒙尼克所有。经许可转载。
2008年12月5日早上,我从塑料送报袋里取出《纽约时报》,展开报纸,读到头版头条:“H.M.,令人难忘的失忆症患者,享年82岁去世。”
对我来说,他当然是令人难忘的。1971年秋天,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心理学教科书中第一次读到关于H.M.的报道,当时距离那场剥夺了他大部分现有记忆和形成新记忆能力的实验性手术还不到二十年。生活在永恒的“当下”的想法似乎令人震惊,我和班上大约两百名其他学生一起,试图想象这种存在会是什么样子。当然,我失败了。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关于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作为一名科学记者,每当我写到涉及记忆科学的故事时,我都会回到H.M.的案例。然而,我从不知道他的名字,这要归功于布伦达·米尔纳和苏珊娜·科尔金的绝对坚持,这两位科学家研究了他五十年,在他生前一直保持匿名。但最终,在第七段中出现了他的名字:“星期二晚上5:05,”报道写道,“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在世界范围内仅被称为H.M.,以保护他的隐私——因呼吸衰竭在康涅狄格州温莎洛克斯的一家疗养院去世。”
2015年夏天,我坐在苏珊娜·科尔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与她谈论她与亨利的长期关系,既是作为一名科学家,也是作为他母亲去世后他最亲近的人。我现在正在撰写关于朗尼·苏·约翰逊的文章,她是另一位失忆症患者,病情与莫莱森的非常相似。(约翰逊的母亲和姐姐,她的主要照顾者,已决定公开她的全名,以便帮助宣传对大脑研究的需求)。
我询问了莫莱森的去世,以及她为了迎接他的离世而计划了几十年的尸检研究。“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这项研究,”她说,然后期待地看着我。我茫然地看着她。 “你的下一个问题,”她提示我,“应该是‘为什么?’”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什么?”我困惑地问道。“为什么,”她继续说,“七年后,我们对他的大脑细节一无所知?” 现在她提到了,七年似乎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这仅仅代表了科学缓慢而谨慎的过程。
我错了。
莫莱森去世后,他的遗体立即被送往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在那里他的大脑被小心地取出并保存。由于手术记录、X光片、CAT扫描和MRI,神经科学家和神经解剖学家大致了解了他的大脑哪些部分在旨在治愈他顽固性癫痫的手术中被破坏了。外科医生威廉·斯科维尔切除了亨利海马体的前部,以及他的大部分内嗅皮层、鼻周皮层和海马旁皮层,现在这些都被理解为对记忆至关重要。斯科维尔还取出了杏仁核,杏仁核负责处理情绪体验。
与此同时,广泛的记忆测试已经探测了他记忆丧失的程度(这是巨大的)。但是,如果不精确地知道取出了多少器官以及哪些器官——以及至关重要的是,他大脑中未触及的部分在细节上是什么样的——科尔金和其他科学家就无法知道他的大脑一开始是否异常。也许他严重的癫痫症造成了一些损害,这可能导致了他的记忆问题。
因此,莫莱森的大脑与他的身体轻轻分离,并交给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神经科学家雅科波·安内塞,他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实验室,专门用于为未来的研究准备它。安内塞明白,尽可能完好地保存亨利的大脑是多么重要。“我记得其他著名大脑的不幸命运,”他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你知道爱因斯坦的大脑发生了什么事,对吧?”
我知道那个离奇的故事。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55年去世时,医院病理学家威廉·哈维取出了大脑,并将其切成两百多小块。哈维分发了一些碎片给研究人员,但将大部分碎片放在几个梅森罐子里,浸泡在酒精中。他最终去了堪萨斯州威奇托市,记者史蒂文·利维于1978年追踪到了他。爱因斯坦腌制的大脑仍然在罐子里,堆在哈维地下室的一堆箱子下面。最终,一些碎片被费城的穆特博物馆收藏。您可以在那里参观它们,在那里您还可以看到从小格罗弗·克利夫兰嘴里取出的肿瘤;约翰·威尔克斯·布斯胸部的组织切片;著名的连体(“暹罗”)双胞胎昌和恩·邦克的共享肝脏;以及各种囊肿、肿瘤和畸形。哈维给实际科学家的少数爱因斯坦大脑样本的研究成果很少,其中一些结果被证明是有问题的。
相比之下,安内塞会将莫莱森的大脑冷冻,然后将其切成两千多片薄片,每片只有七十微米厚。(一微米等于0.000039英寸;一根人发大约一百微米厚。)然后,科学家们将能够使用显微镜和其他技术观察这些切片,以精确了解大脑的样子,直到细胞水平。
耗时五十三小时的细致切片工作(被拍摄和网络直播)几乎正好发生在莫莱森去世一年后。“大脑切得很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神经科学家大卫·阿马拉尔告诉我。“这没有问题。但是……”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从我的科学角度来看,有很多不必要的作秀。” 阿马拉尔认为,安内塞正在利用这次活动来吸引捐款,以支持他所谓的脑观测站。该组织网站上写道:“脑观测站致力于保持开放科学的最高标准,与其他研究人员和公众分享我们在实验室中创建的所有图像和数据。”
然而,至少根据阿马拉尔和去年去世的科尔金的说法,事情并非完全如此。正如安内塞所承诺的那样,许多切片被安装在载玻片上,其余的则被保存起来以备将来安装。但这显然几乎就是全部。阿马拉尔说,通常情况下,像安内塞这样的科学家会继续与其他神经科学家建立合作关系,以研究如此有价值的标本。“例如,”他说,“我的专长是海马体,所以应该联系我或像我这样的人来进行这些研究。” 大脑的其他部分应该由其他专家检查。但实际上,阿马拉尔说,“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科尔金与阿马拉尔和其他人交谈,试图看看可以做些什么。“我们试图干预,”阿马拉尔说,“但仍然什么也没发生。” 科尔金说,安内塞“结果证明是一个糟糕的合作者。他基本上没有履行他的协议,从而使科学研究戛然而止。” 安内塞确实在2013年在《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亨利大脑的结构性损伤,以及“深部白质中的弥漫性病变和左眶额皮层中的一个小的、局限性的病变”。然而,根据被列为该论文合著者的科尔金的说法,这并不等同于完整的病理报告。
安内塞驳斥了这些指责。“令人遗憾的是,”他通过电子邮件说,“一些同事对我在H.M.方面的工作产生了这种印象。多年来,神经病理学检查的问题已被多次提出,这只是总体计划工作的一部分,并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的善意和促进该过程的具体行动。” 他写道,在机构层面,“存在许多超出我控制范围的延误。我认为,困难是由于未能直接、有效和透明地沟通期望和意图而引起的。这有时非常令人沮丧,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整个过程中对我的特权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他说,切割和保存亨利大脑的所有资金都来自他自己的拨款,没有任何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或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贡献。他要求保证脑观测站在任何科学出版物中都将获得适当的认可,并且它将在科学中发挥长期作用。“奇怪的是,”他写道,“我无法获得合适的回应。事实上,在某个时候之后,我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回应。”
科尔金并不这么认为。她说,最终,她只是厌倦了试图从安内塞那里撬出信息。她争取了麻省理工学院、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管理人员的帮助,以迫使解决问题。最终,高层管理人员同意将亨利的大脑转移到另一个机构——具体而言,转移到阿马拉尔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实验室。“这花了很长时间来谈判,”阿马拉尔说,“整个过程并没有得到安内塞博士的促进。”
安内塞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实验室被关闭了,当我和他通电话时,在我了解所有这些背景故事之前,他告诉我他正在寻找资金,为脑观测站寻找一个新的家。在我听到科尔金和阿马拉尔的指责后,我通过电子邮件询问安内塞,为什么他的大学同意将亨利的大脑和其他材料的保管权交给另一个实验室。他并没有真正回答。“藏品的转移,”他写道,“在没有具体的科学或后勤原因的情况下,是在机构层面经过谈判后进行的,这远远超出了我的管辖范围。我于今年 [2015 年] 2 月辞去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职务,因为虽然我尊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授权领导层认为该解决方案符合大学的最佳利益,但他们的决定最终与我的实验室和项目的长期成功不符,这些实验室和项目现在由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管理。”
现在大脑已经重新安置,研究终于开始认真进行。阿马拉尔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开始数字化安内塞准备的载玻片,创建将在网上发布的高分辨率图像。他们与一位阿马拉尔称之为“非常受人尊敬的神经病理学家”的人达成协议,仔细检查组织中可能导致亨利认知能力下降的疾病。他们已经开始组建几个专家联盟,他们将研究大脑的特定部分,试图精确地了解六十多年前莫莱森的记忆制造装置被破坏时发生了什么。“我们将能够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描述,”阿马拉尔说,“关于移除了什么,完好无损的是什么。”
就这样,在 1950 年代开启现代记忆研究的大脑将为科学做出最后的、至关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