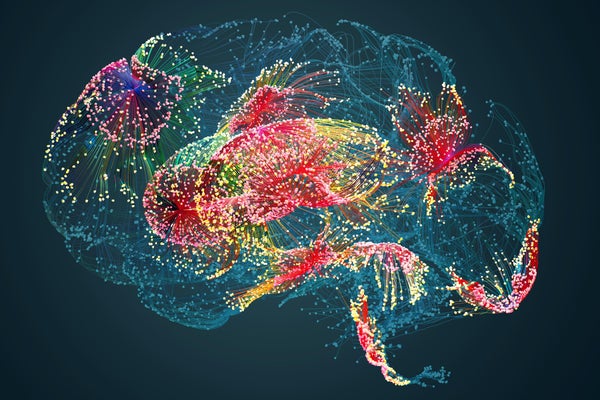大脑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件家具,受制于与小行星、电子或光子相同的物理定律。从表面上看,其三磅重的神经组织似乎与量子力学几乎没有关系,量子力学是所有物理系统的教科书理论基础,因为量子效应在微观尺度上最为明显。然而,新提出的实验有望弥合微观和宏观系统(如大脑)之间的差距,并为意识之谜提供答案。
量子力学解释了一系列无法用日常经验形成的直觉来理解的现象。回想一下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其中猫存在于叠加态中,既是死的又是活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没有这种不确定性——猫要么是死的,要么是活的。但量子力学方程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刻,世界都由许多这样的共存状态组成,这种张力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物理学家。
宇宙学家罗杰·彭罗斯在 1989 年大胆地提出,每当叠加的量子态坍缩时,就会发生一个意识瞬间。意识的起源和量子力学中所谓的波函数坍缩这两个基本的科学谜团是相关的,这一想法引发了巨大的兴奋。
支持科学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当今塑造我们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彭罗斯的理论可以建立在量子计算的复杂性之上。考虑一个量子比特,即量子信息理论中的信息单位,它存在于逻辑 0 和逻辑 1 的叠加态中。根据彭罗斯的说法,当这个系统坍缩成 0 或 1 时,就会产生一个意识体验的闪烁,用一个经典的比特来描述。
彭罗斯与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梅罗夫共同提出,这种坍缩发生在微管中,微管是管状的细长结构蛋白,构成细胞骨架的一部分,例如构成中枢神经系统的细胞。
这些想法从未被科学界采纳,因为大脑是潮湿和温暖的,不利于叠加态的形成,至少与现有的量子计算机相比是这样,现有的量子计算机在比室温低 10,000 倍的温度下运行,以避免破坏叠加态。
当应用于两个或多个纠缠的量子比特时,彭罗斯的提议存在缺陷。测量其中一个纠缠的量子比特会立即揭示另一个量子比特的状态,无论它们相距多远。它们的状态是相关的,但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并且根据标准量子力学,纠缠不能用于实现超光速通信。然而,根据彭罗斯的提议,参与纠缠态的量子比特共享一种意识体验。当其中一个量子比特呈现确定的状态时,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建立一个能够以超光速传输信息的通信通道,这违反了狭义相对论。
我们认为,数百个量子比特(如果不是数千个或更多)的纠缠对于充分描述任何一个主观体验的现象学丰富性至关重要:颜色、运动、纹理、气味、声音、身体感觉、情感、思想、记忆碎片等等,这些构成了生命本身的感受。
在我们和同事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Entropy上的一篇文章中,我们颠倒了彭罗斯的假设,提出每当系统进入量子叠加态时,而不是坍缩时,就会产生体验。根据我们的提议,任何进入具有一个或多个纠缠叠加量子比特的状态的系统都将体验到意识的瞬间。
聪明的读者,您现在肯定在对自己说:但是等一下——我从不有意识地体验叠加态。任何一种体验都具有明确的品质;它是一回事而不是另一回事。我看到一种特定的红色阴影,感觉到牙痛。我不会同时体验红色和非红色,疼痛和非疼痛。
任何意识体验的确定性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中。多世界观点是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在 1957 年首次提出的形而上学立场,它将时间的演化视为一棵巨大的分支树,量子事件的每一种可能结果都会分裂出自己的宇宙。一个进入叠加态的量子比特会诞生两个宇宙,其中一个宇宙中量子比特的状态为 0,而在孪生宇宙中,除了量子比特的状态为 1 之外,一切都相同。
纠缠可能为脑科学家提供其他东西,因为它为所谓的绑定问题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解决方案,即每种体验的主观统一性,长期以来,这种统一性一直对意识研究构成关键挑战。考虑一下看到自由女神像:她的脸、头上的皇冠、她举起的右手上的火炬等等。所有这些区别和关系都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感知,其基质可能是许多相互纠缠的量子比特。
为了使这些深奥的想法具体化,我们提出了三个实验,这些实验将越来越多地塑造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第一个实验,目前正在进行中,这要归功于位于圣莫尼卡的 Tiny Blue Dot 基金会的资助,旨在为量子力学与神经科学的相关性提供证据,这两个非常容易接近的试验平台:微小的果蝇和大脑类器官,后者是由人类诱导的多能干细胞生长而成的数千个神经元的扁豆大小的集合体。众所周知,惰性气体氙气可以在动物和人身上充当麻醉剂。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一项实验声称,其麻醉效力(以诱导动物无法移动的气体浓度衡量)取决于氙气的特定同位素。元素的两种同位素包含相同数量的带正电的质子,但原子核中包含不同数量的不带电的中子。同位素的化学性质(即它们与什么相互作用)大致相似,即使它们的质量和磁性略有不同。
如果果蝇和类器官可以用来检测不同的氙同位素,那么我们将开始寻找惰性气体(并且与蛋白质或其他分子结合保持疏远)实现这一目标的精确机制。是这些同位素的质量(131 个核子与 132 个核子)的微小差异造成了差异吗?还是它们的核自旋,原子核的量子力学性质?这些氙同位素的核自旋差异很大;有些同位素的自旋为零,另一些同位素的自旋为 1/2 或 3/2。
这些氙实验将为第二个后续实验提供信息,在第二个后续实验中,我们将尝试将量子比特耦合到大脑类器官,从而使纠缠在生物量子比特和技术量子比特之间传播。最终的实验(目前仍纯粹是概念性的)旨在通过以纠缠的方式将工程量子态耦合到人脑来增强意识。然后,人可能会体验到扩展的意识状态,就像在服用死藤水或裸盖菇素的影响下所访问的状态一样。
量子工程和脑机接口的设计都在快速发展。利用量子科学和技术直接探测和扩展我们的意识思维可能并非超出人类的创造力。
这是一篇观点和分析文章,作者或作者表达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大众科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