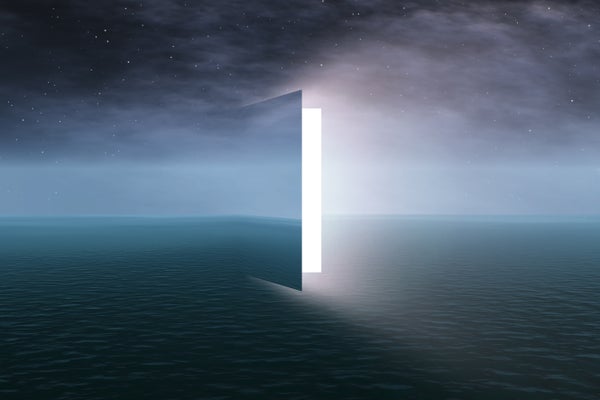在查尔斯·狄更斯备受喜爱的小说《圣诞颂歌》中,脾气暴躁的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在圣诞节过去和现在的幽灵向他展示他的残忍和自私如何伤害他人时,他仍然无动于衷。只有当未来圣诞节的幽灵以他的墓碑的形式让斯克鲁奇直面自己的无常时,这个老吝啬鬼才开始对他人表现出仁慈和同情。
新冠病毒大流行使我们所有人都更接近自己的无常。面对临时太平间的照片和报道死亡人数的可怕头条新闻,我们看到,从汤姆·汉克斯到鲍里斯·约翰逊,我们所有人都很脆弱——这是一个我们在威胁较小的时期会从脑海中推开的事实。
但是,我们对这种增强的死亡感的反应可能会令人眼花缭乱地不一致。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令人惊叹的人们在大流行期间挺身而出帮助他人:从一位99岁的老兵在他的花园里走圈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筹集了3300万美元,到一位皇家女帽制造商开始为医院工作人员制作面罩。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人囤积枪支,囤积罐头食品和卫生纸,并通过违抗科学来使他人面临危险。
支持科学新闻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 订阅来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未来有关发现和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这些截然相反的反应——以及我们如何遵循我们最好的本能而不是最坏的本能。这一切似乎都归结于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正如文化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在1973年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反思自我的能力给人类带来了问题:对自我存在的意识意味着它有一天会停止存在。在心理学中,恐惧管理理论研究当死亡对我们变得突出时,我们如何反应。在他们的书《核心之虫》中,谢尔顿·所罗门和他的同事描述了恐惧管理理论是如何从假设开始的,即像其他生物一样,人类具有自我保护和生存的本能。但与其它生物不同的是,我们的智力能力让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终将死去。
反思死亡是痛苦的,但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拉比约书亚·L·利布曼在他的书《心灵的平静》中所写的那样,“死亡不是生命的敌人,而是它的朋友,因为正是我们对生命有限的认识才使得它如此珍贵。”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在一组经历过院外心脏骤停的患者中,那些最接近濒死体验的患者变得更能容忍他人的差异,更好地理解自己,更欣赏自然,并报告说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
在他告别的《纽约时报》专栏中,已故的神经学家和作家奥利弗·萨克斯写道,在得知自己患有晚期癌症后,他并没有结束生命。“相反,”他写道,“我感到无比地活着,我希望并希望在剩下的时间里加深我的友谊,向我爱的人告别,写更多的东西,如果我有力气就去旅行,以达到新的理解和洞察力水平。”
在一系列研究中,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和她的合著者表明,我们选择如何度过我们宝贵的时间取决于我们认为还剩下多少时间。一旦生命的脆弱性成为一个个人的真相,而不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哲学概念,我们就更有能力庆祝剩下的每一天和经历,而不是专注于日常的烦恼。承认我们的无常让我们更加关注生活中的小瞬间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您是否注意到街上人们彼此微笑的次数更多,或者他们在眼神交流和问候方面变得更自由?也许您不经常见到的人正在与您建立Zoom通话以重新取得联系。或者,也许您正在与亲人一起开辟更有意义的日常活动,从一起做饭到定期视频聊天。在大流行期间,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我们的机会和人际关系正在倒计时。
人类有着利用生命的脆弱性来更好地珍惜时间的历史。中世纪的僧侣在他们的书桌上放着一个人的头骨,以帮助他们反思自己的无常。17世纪的绘画流派,称为“虚空”,具有相同的功能——例如,通过描绘一个在枯萎的花束或与人类头骨并排的成熟水果旁滴答作响的金怀表。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建议让死亡进入我们的意识,以激发我们对生活更深的欣赏和帮助人类同胞的更大动力。
有些人将这种意识推向极限。亚历克斯·霍诺尔德独自攀登山脉的陡峭表面,例如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埃尔卡皮坦峰——没有绳索或支撑。“我觉得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任何一天死去,”他在纪录片《徒手攀岩》中说。“徒手攀岩让它感觉更加直接和真实……当你没有绳索攀爬时,后果显然要高得多——专注程度要高得多。”
接近死亡可以让许多人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并努力做出他们最好的贡献。它也使一些人更加亲社会——也就是说,更愿意给予他人。这种效果的部分原因是,为社会做出贡献是永远活下去的一种方式。对死亡的频繁提醒加强了“将自己的物质投入到能够超越自我的生命和工作形式中的愿望,”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的退休心理学教授约翰·科特在1984年的一本书中写道。
在一项名为“斯克鲁奇效应”的系列研究中,当时在德国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的研究员伊娃·乔纳斯和她的同事发现,当人们在殡仪馆前接受采访时,他们对慈善机构更为有利——例如,他们认为某个慈善机构对社会更有益——而不是在几个街区之外接受采访。当美国参与者有机会向一家美国慈善机构捐款时,那些被要求写下自己死亡的人的捐款比那些被要求写牙痛的人高出约400%。
有趣的是,然而,同一研究中的参与者并没有向一家外国慈善机构捐出更高的捐款,因为那会使与他们不同的人受益。正如这一发现所表明的那样,当死亡突出时(就像现在的新冠病毒一样),我们可以走向任何一个方向:我们可能会受到激励做出积极的改变,但我们也可能更容易陷入陷阱,陷入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偏见。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当时都在亚利桑那大学的亚伯兰·罗森布拉特和杰夫·格林伯格让真正的法官阅读了一名被指控从事卖淫行为的女性的假设检察官笔记。在要求法官设定她的保释金之前,研究人员让他们填写了一份性格问卷。一些法官收到了一个问题,要求他们简要描述当他们想到自己的死亡时的情绪。“我想我会为我的家人感到非常难过,他们会想念我,”一个典型的回答写道。
其他法官没有得到任何以死亡为导向的问题。他们将保释金定为 50 美元——这是该犯罪的平均水平。那些被引导思考自己道德的人更加严厉:他们设定的平均保释金为 455 美元,是控制组法官的九倍之多。研究结束后,法官们坚持认为回答有关他们死亡的问题不可能影响他们的法律决定。毕竟,他们的工作是成为根据事实衡量案件的理性专家。但证据表明并非如此。
为什么当人们思考死亡时,有时会变得思想封闭和道貌岸然,而不是专注于帮助他人?因为我们的道德、群体和国家将在我们之后继续存在。如果我们不小心,对死亡的焦虑会让我们执着于当地的文化,这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生命”。因此,被鼓励反思死亡的法官不仅想给那个女人一记耳光,还想给她“应得”的惩罚,因为她违反了道德。如果让死亡意识让你感到焦虑而不是反思,你就会试图通过道德说教、民族主义、攻击其他文化甚至支持战争来积极地保护你的世界观。
这是死亡意识的另一面:当我们的反应从反思转向焦虑时,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加自我保护。我们成为自私偏见的牺牲品,多元化努力困扰着我们——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亚当·格兰特和杜克大学教授金伯利·韦德·本佐尼描述了这种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提出战争威胁的民族主义政客会赢得支持者来阻止外国人:思考我们可能的死亡会把我们变成自以为是、好斗、目光短浅的仇外者。
我们都有权选择如何应对我们在大流行期间正在经历的死亡意识。当我们能够反思死亡而不屈服于对其的焦虑时,我们可能会做出选择,帮助我们做出最好的贡献并改善世界,而不是退缩或猛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