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对自己的看法是扭曲的。
你的“自我”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摆在你面前。只需窥视内部并阅读:你是谁,你的喜好和厌恶,你的希望和恐惧;它们都在那里,准备被理解。这种观念很流行,但可能完全是错误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并没有特权去了解我们是谁。当我们试图准确评估自己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雾里摸索。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艾米丽·普罗宁,她专门研究人类的自我认知和决策,将对特权访问的错误信念称为“内省错觉”。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扭曲的,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结果,我们的自我形象与我们的行为关系出奇地小。例如,我们可能绝对确信自己富有同情心和慷慨,但仍然在寒冷的一天径直走过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关于支持科学新闻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屡获殊荣的新闻报道 订阅。通过购买订阅,您正在帮助确保有关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发现和想法的具有影响力的故事的未来。
根据普罗宁的说法,这种扭曲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想吝啬、傲慢或自以为是,所以我们假设我们不是任何这些东西。作为证据,她指出了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不同看法。我们毫不费力地认识到我们的办公室同事对另一个人是多么的偏见或不公平。但我们没有考虑到我们可能会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行事:因为我们打算在道德上是善良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也可能是有偏见的。
普罗宁在许多实验中评估了她的论点。其中,她让她的研究参与者完成一项测试,该测试涉及将面孔与个人陈述相匹配,这些陈述本应评估他们的社交智力。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告知他们失败了,并被要求指出测试程序中的弱点。尽管受试者的意见几乎肯定是带有偏见的(他们不仅被认为测试失败了,而且还被要求批评它),但大多数参与者表示他们的评估是完全客观的。在评判艺术作品时情况也大致相同,尽管使用有偏见的策略评估绘画质量的受试者仍然认为他们自己的判断是公正的。普罗宁认为,我们天生就被设定为掩盖自己的偏见。
“内省”这个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隐喻吗?会不会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审视自己,正如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所暗示的那样,而是在产生一个奉承的自我形象,否认我们所有人都有的缺点?关于自我认知的研究已经为这个结论提供了很多证据。尽管我们认为我们正在清晰地观察自己,但我们的自我形象受到仍然无意识的过程的影响。
2. 你的动机通常对你来说是一个完全的谜。
人们对自己有多了解?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研究人员遇到了以下问题:要评估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就必须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调查人员使用各种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他们将测试对象的自我评估与受试者在实验室情况或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比较。他们可能会要求其他人,例如亲戚或朋友,也对受试者进行评估。他们还使用特殊方法探测无意识的倾向。
为了衡量无意识的倾向,心理学家可以应用一种称为内隐关联测试 (IAT) 的方法,该方法由华盛顿大学的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和他的同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发,用于揭示隐藏的态度。从那时起,人们设计了许多变体来检查焦虑、冲动性和社交能力等特征。该方法假设瞬时反应不需要反思;因此,个性的无意识部分会浮出水面。
值得注意的是,实验者试图确定与某人相关的词语与某些概念的联系有多紧密。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当屏幕上出现描述外向性等特征的词语(例如“健谈”或“精力充沛”)时,参与者被要求尽快按下按键。当他们在屏幕上看到与自己相关的词语(例如他们自己的名字)时,他们也被要求按下同一个按键。当出现内向特征(例如“安静”或“内向”)或当该词语涉及其他人时,他们应该按下不同的按键。当然,在许多次测试运行中,词语和按键组合被切换了。例如,如果当与参与者相关的词语跟随“外向”出现时,反应更快,那么可以假设外向性可能是一个人自我形象的组成部分。
这种“内隐”的自我概念通常与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自我评估只有微弱的对应关系。人们在调查中传达的形象与他们对情感色彩浓厚的词语的闪电般的反应几乎无关。一个人的内隐自我形象通常可以很好地预测他或她的实际行为,尤其是在涉及紧张或社交能力时。另一方面,问卷调查可以更好地了解诸如责任心或对新体验的开放性等特质。德国明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米特亚·巴克解释说,旨在引发自动反应的方法反映了我们个性的自发或习惯性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责任心和好奇心需要一定程度的思考,因此可以通过自我反省更容易地进行评估。
3. 外在表现告诉人们很多关于你的信息。
许多研究表明,我们最亲近的人往往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正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西米内·瓦齐尔所表明的那样,特别是两个条件可能使其他人更容易认识到我们真正的身份:首先,当他们能够从外在特征中“读出”一种特质时;其次,当一种特质具有明显的正面或负面效价时(例如,智力和创造力显然是令人向往的;不诚实和自我中心则不是)。当涉及到更中性的特征时,我们对自己的评估与他人的评估最接近。
通常最容易被他人解读的特征是那些强烈影响我们行为的特征。例如,天生善于交际的人通常喜欢说话和寻求陪伴;不安全感通常表现为诸如绞着双手或转移视线等行为。相比之下,沉思通常是内在的,在自己的思想范围内展开。
我们经常对我们对他人的影响视而不见,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面部表情、手势和肢体语言。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的眨眼表明压力,或者我的姿势塌陷暴露了某件事对我来说有多么沉重。因为观察自己是如此困难,我们必须依靠他人的观察,尤其是那些了解我们的人的观察。除非别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影响他们,否则很难知道我们是谁。

没有安全感?谁,我?!我们常常对我们对他人的影响了解甚少。图片来源: Terry Mcclendon Getty Images
4. 保持一定距离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写日记、暂停进行自我反省以及与他人进行探究性对话有着悠久的传统,但这些方法是否能让我们了解自己还很难说。事实上,有时做相反的事情——例如放手——更有帮助,因为它提供了一些距离。2013 年,现在在多伦多大学的埃里卡·卡尔森回顾了关于正念冥想是否以及如何提高自我认知的文献。她指出,它通过克服两个巨大的障碍来提供帮助:扭曲的思维和自我保护。正念的练习教会我们允许我们的想法简单地飘过,并尽可能少地认同它们。毕竟,想法“只是想法”,而不是绝对的真理。通常,以这种方式走出自我,简单地观察思想在做什么,可以培养清晰度。
深入了解我们的无意识动机可以增强情绪健康。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的奥利弗·C·舒尔特海斯表明,随着我们的意识目标和无意识动机变得更加一致或协调,我们的幸福感往往会增长。例如,如果这些目标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就不应该为了从事一份能给我们金钱和权力的职业而拼命工作。但是我们如何实现这种和谐呢?例如,通过想象。尝试尽可能生动和详细地想象一下,如果你最热切的愿望成真,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它真的会让你更快乐吗?我们经常屈服于过度追求高目标的诱惑,而没有考虑到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所需的所有步骤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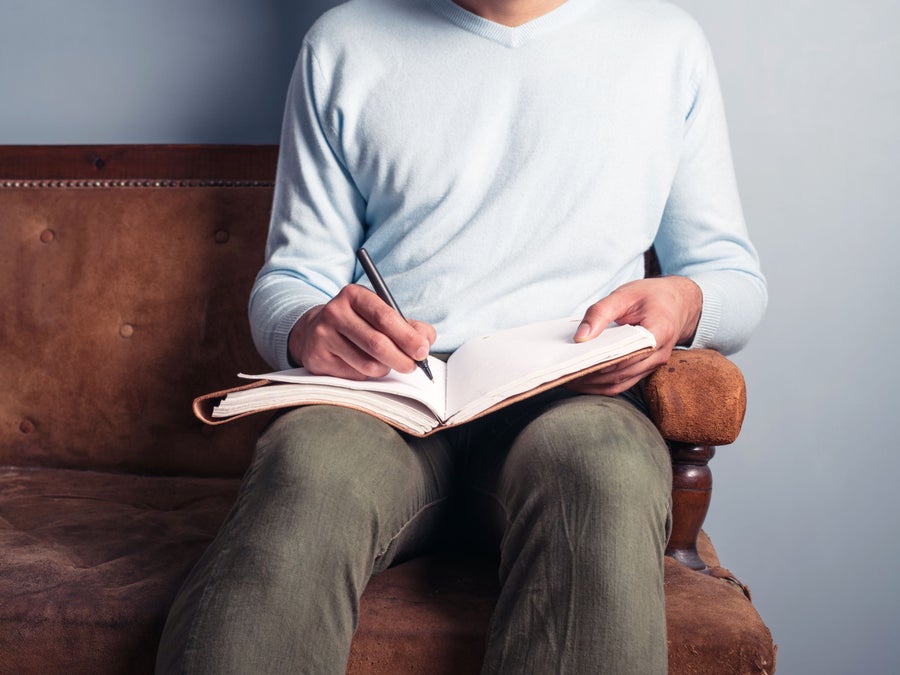
通过日记进行自我发现?那些以一定距离审视自己的人——例如,在独处时——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5. 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比实际更擅长某件事。
你熟悉邓宁-克鲁格效应吗?它认为,人越无能,就越意识不到自己的无能。这种效应以密歇根大学的大卫·邓宁和纽约大学的贾斯汀·克鲁格的名字命名。
邓宁和克鲁格给他们的测试对象布置了一系列认知任务,并要求他们估计自己做得有多好。充其量,25% 的参与者或多或少地以现实的态度看待自己的表现;只有少数人低估了自己。在测试中得分最差的四分之一受试者真的没有达到目标,他们极大地夸大了自己的认知能力。吹嘘和失败是否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正如研究人员强调的那样,他们的工作突出了自我认知的普遍特征: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忽视自己的认知缺陷。伦敦大学学院的心理学家阿德里安·弗纳姆表示,感知智商和实际智商之间的统计相关性平均只有 0.16——委婉地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表现。相比之下,身高和性别之间的相关性约为 0.7。
那么,为什么潜在表现和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呢?难道我们都不想现实地评估自己吗?这肯定会避免我们浪费大量精力,或许还能避免一些尴尬。答案似乎是,适度夸大自尊心是有一定好处的。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雪莱·泰勒和华盛顿大学的乔纳森·布朗的评论,玫瑰色的眼镜往往会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和表现。另一方面,患有抑郁症的人倾向于在自我评估中保持残酷的现实主义。一个美化的自我形象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度过日常生活的起伏。
6. 贬低自己的人更频繁地经历挫折。
尽管我们大多数同龄人都对自己的诚实或智力抱有过于积极的看法,但有些人却遭受着相反的扭曲:他们贬低自己和自己的努力。童年时期经历的蔑视和贬低,通常与暴力和虐待有关,会引发这种消极情绪——反过来,这会限制人们可以完成的事情,导致不信任、绝望甚至自杀念头。
认为具有负面自我形象的人正是那些想要过度补偿的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然而,正如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威廉·斯旺合作的心理学家所发现的那样,许多被自我怀疑折磨的人寻求对他们扭曲的自我认知的确认。斯旺在一项关于婚姻幸福感的研究中描述了这种现象。他询问夫妻双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感受到伴侣支持和重视的方式,以及他们在婚姻中的幸福程度。正如预期的那样,那些对自身态度更积极的人发现,他们从另一半那里获得的赞扬和认可越多,他们在关系中就越满意。但是,那些习惯性地挑剔自己的人,当他们的伴侣将他们的负面形象反映给他们时,他们在婚姻中会感到更安全。他们没有要求尊重或赞赏。相反,他们想听到的正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很无能。”
斯旺基于这些发现提出了他的自我验证理论。该理论认为,我们希望别人像我们看待自己一样看待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实际上会激怒他人对他们做出负面回应,以证明他们是多么的毫无价值。这种行为不一定是受虐狂。它是对连贯性渴望的症状:如果其他人以确认我们自我形象的方式回应我们,那么世界就应该是这样。
同样,那些认为自己是失败者的人会竭尽全力不成功,从而积极地促成自己的失败。他们会错过会议,习惯性地忽视分配的工作,并与老板发生冲突。斯旺的方法与邓宁和克鲁格的过度估计理论相矛盾。但两派可能都是正确的:过度膨胀的自我当然很常见,但负面的自我形象也并不少见。
7. 你在不知不觉中欺骗自己。
根据一项有影响力的理论,我们自我欺骗的倾向源于我们渴望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为了显得有说服力,我们自己必须相信自己的能力和真实性。支持这一理论的观察是,成功的操纵者通常都非常自负。例如,优秀的销售人员会散发出一种具有感染力的热情;相反,那些怀疑自己的人通常不擅长甜言蜜语。实验室研究也支持这一点。在一项研究中,如果参与者在面试中能令人信服地声称自己在智商测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们就会获得报酬。候选人在表现中付出的努力越多,他们自己就越相信自己拥有高智商,即使他们的实际分数或多或少是平均水平。
我们的自我欺骗已被证明是相当多变的。我们经常灵活地调整它们以适应新的情况。布朗大学的史蒂文·A·斯洛曼和他的同事证明了这种适应性。他们的受试者被要求尽可能快地将光标移动到计算机屏幕上的一个点。如果参与者被告知,在这项任务中高于平均水平的技能反映了高智商,他们会立即专注于这项任务并做得更好。他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认为自己付出了更多努力——研究人员将此解释为成功自我欺骗的证据。另一方面,如果测试对象确信只有笨蛋才能在如此愚蠢的任务中表现良好,他们的表现就会急剧下降。
但是,自我欺骗甚至可能吗?我们能否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自己,而又没有意识到它?当然可以!实验证据涉及以下研究设计:向受试者播放人类声音的录音带,包括他们自己的声音,并要求他们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是否听到自己的声音。识别率会根据录音带的清晰度和背景噪音的大小而波动。如果同时测量脑电波,则阅读中的特定信号可以肯定地表明参与者是否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大多数人听到自己的声音时都会感到有些尴尬。在一项经典研究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鲁本·古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哈罗德·萨凯姆利用了这种沉默寡言,将测试对象的陈述与他们的脑部活动进行了比较。瞧,活动经常发出“那是我!”的信号,而受试者并没有公开地将某个声音识别为他们自己的声音。此外,如果调查人员威胁到参与者的自我形象——例如,告诉他们他们在另一项(不相关的)测试中得分很差——他们就更不容易认出自己的声音。无论哪种方式,他们的脑电波都讲述了真实的故事。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评估了学生在练习测试中的表现,该测试旨在帮助学生评估自己的知识,以便他们能够填补空白。在这里,受试者被要求在设定的时间限制内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鉴于练习测试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他们作弊几乎没有意义;相反,人为抬高的分数可能会导致他们放松学习。那些试图通过使用超出分配完成时间的时间来提高分数的人只会伤害自己。
但是,许多志愿者确实这样做了。无意识地,他们只是想看起来不错。因此,作弊者解释说他们超时是因为他们分心了,并且想要弥补失去的时间。或者他们说,他们伪造的结果更接近他们的“真正潜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解释混淆了因果关系,人们错误地认为,“聪明人通常在考试中表现更好。因此,如果我只是通过比允许的时间多花一点时间来操纵我的考试分数,我也是聪明人之一。”相反,如果人们被告知表现良好表明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更高,他们的表现就会不那么勤奋。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称为诊断性自我欺骗。
8. “真我”对你有好处。
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有一个坚实的本质核心,一个真我。他们真正的身份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道德价值观中,并且相对稳定;其他偏好可能会改变,但真我始终不变。德克萨斯 A&M 大学的丽贝卡·施莱格尔和约书亚·希克斯及其同事研究了人们对真我的看法如何影响他们对自己的满意度。研究人员要求测试对象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日记。结果表明,当参与者做了道德上可疑的事情时,他们会感到与自己最疏远:当他们不诚实或自私时,他们特别不确定自己实际上是谁。实验也证实了自我与道德之间的关联。当测试对象被提醒早期的不当行为时,他们对自己的确定性会受到打击。
耶鲁大学的乔治·纽曼和约书亚·诺布发现,人们通常认为人类内心深处都怀有一个善良的真我。他们向受试者展示了不诚实的人、种族主义者等人的案例研究。参与者普遍将案例研究中的行为归因于环境因素,例如艰难的童年——这些人的真正本质肯定与此不同。这项工作表明,我们倾向于认为,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他们会追求道德和善良。
纽曼和诺布的另一项研究涉及“马克”,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仍然被其他男人所吸引。研究人员试图了解参与者如何看待马克的困境。对于保守的测试对象来说,马克的“真我”不是同性恋;他们建议他抵制这种诱惑。那些持更自由观点的人认为他应该出柜。然而,如果马克被描绘成一个世俗人文主义者,他认为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想到同性伴侣时却有负面情绪,保守派很快将这种不情愿视为马克真我的证据;自由派则将其视为缺乏洞察力或世故的证据。换句话说,我们声称是另一个人个性的核心实际上根植于我们自己最珍视的价值观。“真我”原来是一把道德标尺。
对真我是道德的这种信念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将个人进步而不是个人缺陷与他们的“真我”联系起来。显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积极地提升对自己的评价。安大略省威尔弗里德·劳里埃大学的安妮·E·威尔逊和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的迈克尔·罗斯在几项研究中表明,我们倾向于将更多的负面特征归因于过去的自己——这让我们现在看起来更好。根据威尔逊和罗斯的说法,人们回溯得越远,他们的性格描述就越负面。尽管进步和改变是正常成熟过程的一部分,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已经成为“真正的自己”感觉很好。
假设我们有一个坚实的身份核心可以降低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复杂性。我们周围的人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角色,他们的行为前后不一致,同时又在不断发展。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朋友汤姆和莎拉明天将与今天完全一样,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好人——无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没有对真我的信念,生活甚至可以想象吗?研究人员通过比较不同的文化来研究这个问题。对真我的信念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很普遍。一个例外是佛教,它宣扬稳定的自我不存在。未来的佛教僧侣被教导要看穿自我的虚幻性——它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并且完全可塑。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尼娜·斯特罗明格和她的同事想知道这种观点如何影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向大约 200 名西藏俗人和 60 名佛教僧侣发放了一系列问卷和情景。他们将结果与美国基督徒和非宗教人士的结果,以及印度教徒的结果(他们与基督徒非常相似,认为灵魂的核心,或梵我,赋予人类身份)进行了比较。佛教徒的常见形象是他们非常放松,完全是“无私”的人。然而,西藏僧侣越不相信稳定的内在本质,他们就越有可能害怕死亡。此外,在一个假设的情景中,放弃某种药物可以延长另一个人的生命,他们明显更加自私。近四分之三的僧侣反对虚构的选择,远远超过美国人或印度教徒。自私自利、恐惧死亡的佛教徒?在另一篇论文中,斯特罗明格和她的同事将真我的概念称为“充满希望的幻想”,尽管它可能是有用的。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难以动摇的概念。

佛教徒认为自我是一种幻觉。然而,研究表明,这种信念比相信真我更容易让人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图片来源: Gavin Gough Getty Images
9. 没有安全感的人往往表现得更道德。
没有安全感通常被认为是缺点,但它并非完全不好。对他们是否具有某些积极特质感到不安全的人往往会试图证明他们确实具有这些特质。例如,那些不确定自己是否慷慨的人更有可能向慈善事业捐款。这种行为可以通过实验引出来,方法是给受试者负面反馈——例如,“根据我们的测试,您的乐于助人和合作精神低于平均水平。”人们不喜欢听到这样的判断,最终会向捐款箱捐款。
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德拉任·普雷勒茨用他的自我信号理论解释了这些发现:特定行为对我的评价通常比行为的实际目标更重要。不止少数人坚持节食是因为他们不想显得意志薄弱。相反,经验已经证实,那些确信自己慷慨、聪明或善于交际的人会减少证明这一点的努力。过多的自信会让人自满,并加剧他们想象中的自我与真实的自我之间的鸿沟。因此,那些认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人特别容易比他们想象的更不了解自己。

不确定自己是否慷慨的人通常会向慈善事业捐赠更多。图片来源: Andre Thijssen Getty Images
10.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灵活的,你会做得更好。
人们对自己是谁的理论会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因此,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很容易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斯坦福大学的卡罗尔·德韦克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这种影响。她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特征是可变的,我们就会更倾向于努力改进它。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智商或意志力等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改变的和固有的,我们将很少努力去改进它。
在德韦克对学生、男性和女性、父母和教师的研究中,她收集到一个基本原则:具有僵化自我意识的人会糟糕地接受失败。他们将其视为自己局限性的证据并害怕它;与此同时,对失败的恐惧本身会导致失败。相比之下,那些理解特定才能是可以培养的人会将挫折视为下次做得更好的邀请。因此,德韦克建议采取旨在个人成长的态度。当有疑问时,我们应该假设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学习,并且我们可以进步和发展。
但是,即使是那些具有僵化自我意识的人,他们的性格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固定的。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安德烈亚斯·施泰默表示,即使人们将自己的优势描述为完全稳定,他们也倾向于相信自己迟早会克服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试图想象几年后我们的性格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倾向于诸如:“冷静的头脑和清晰的 focus 仍然是我的一部分,而且我可能会减少自我怀疑。”
总的来说,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性格视为比实际更静态,这可能是因为这种评估提供了安全感和方向。我们希望认识到自己的特定特征和偏好,以便我们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归根结底,我们创造的自我形象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的一种安全港湾。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研究人员表示,自我认知比人们想象的更难获得。当代心理学从根本上质疑了我们可以客观和最终地了解自己的观点。它明确指出,自我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不断适应变化环境的过程。我们如此频繁地将自己视为比实际更称职、更道德和更稳定,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的适应能力。
